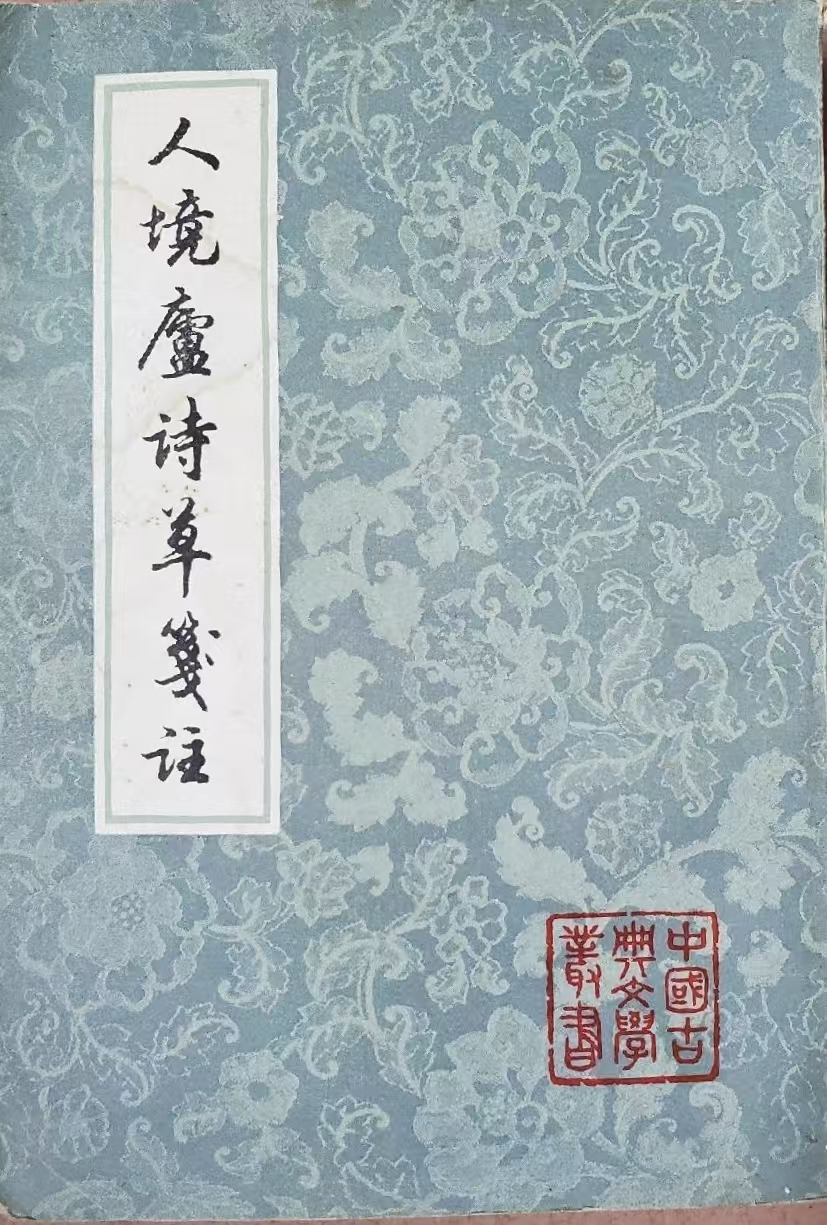
《人境庐诗草笺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钱仲联先生的《人境庐诗草笺注》是他出版最早的一部古籍整理、笺注的著作,也是他除《海日楼诗注》(《沈曾植集校注》)外,用力最勤的一部。该书最早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于1936年。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于1957年首次出版,并于198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2000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人境庐诗草》在列,所用即钱仲联先生的笺注本。该版有所修订,钱先生在该版书末有一“2000年版跋”,交代了该书简单的出版流程,并提及了诸版的修改情况:
《人境庐诗草笺注》初版本,连史纸线装本三册,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多次重印,最后一次印本为一九八一年六月版。商务本原有之陈柱、冯振、王蘧常三先生之序及余自序,俱被重印本删去,注中所引曾国藩日记及诗句亦被删去,其他笺注内容,颇多更易,与商务本互有短长。兹合各本,取长补短,如恢复所引曾诗,增注唐才质详细生平;原注佛典,转引者多,兹直接从《大藏经》改采切当之经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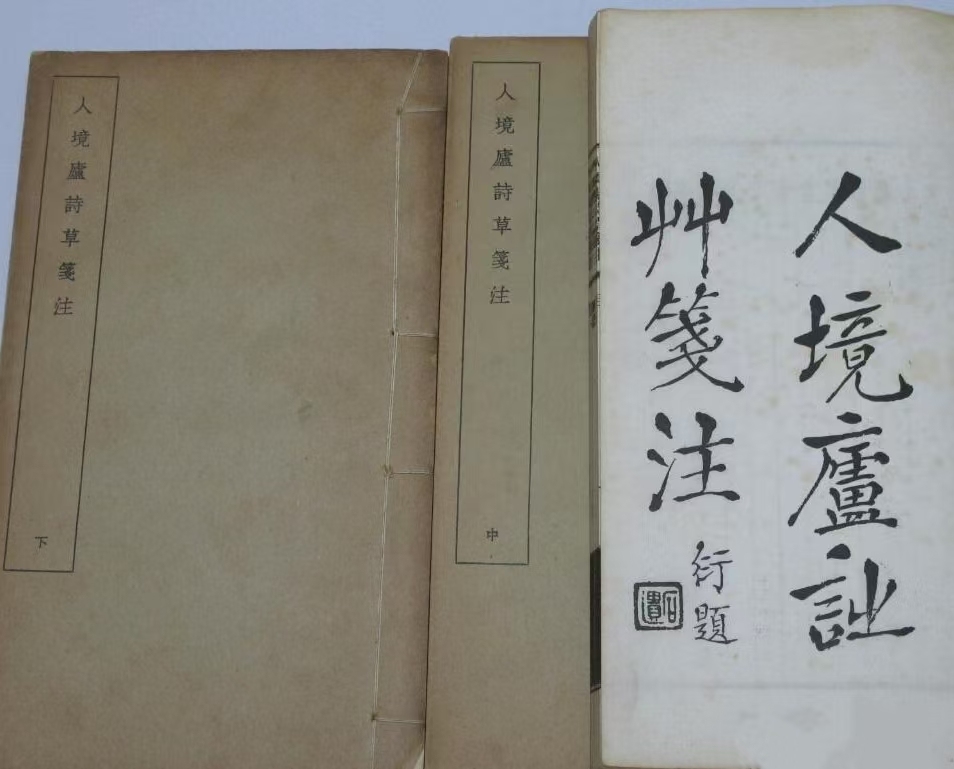
《人境庐诗草笺注》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上中下册
跋文中提到该书建国后出版的版本对原1936年商务版似有不小的删改。将1936年商务版与建国后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版两相对照,确实,1957年版仅保留了黄遵宪诗集的自序和康有为为黄遵宪诗集写的序,将钱仲联的自序,陈柱、冯振、王蘧常三人为钱仲联《笺注》所写序删去,这应该是为了突出出版该书乃以诗集为主,笺注为阅读辅助的缘故。1936年版中,在注释黄诗时,钱仲联先生引用了大量曾国藩的诗文作为书证。如卷一《感怀》“万世循轨辙”引曾国藩诗“历世循旧辙”;《潮州行》“扶床面色灰”引曾国藩诗“客子扶床面已灰”等,在1957年版中皆被删去。而《感怀》“上溯考据家”引曾国藩日记“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本孔门文学之科”,则被改换成“姚鼐《复秦小岘书》:天下学问文章,有义理、文章、考据之分,异趋而同为不可废”。这种删改,自然是因为建国后对曾国藩的评价问题所致。曾国藩在晚清民国知识分子圈中被认为是道德文章楷模,但他在清廷应对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所以后来范文澜先生曾写书批判曾国藩,基本为建国初期对曾的看法定了基调。如此,在当时,一本书中如不加批判地大量引用曾国藩的诗文,显然不大合适。1936年版《人境庐诗草笺注》之大量引用曾国藩诗文,倒可看出钱仲联先生对黄遵宪诗的看法,即他的诗歌技法有学习曾国藩的地方。黄诗自序中说今人写诗当“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入诗”,这与曾国藩在《大潜山房诗题语》中评价宋诗“山谷学杜公七律,专以单行之气运于偶句之中;东坡学太白,则以长古之气运于律句之中。樊川七律,亦有一种单行票姚之气”云云颇为相似。1981年《人境庐诗草笺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所引曾诗也未恢复,而钱仲联先生又在书前加了一篇论黄遵宪及黄遵宪诗的长文,讲到对前人的承袭,也只及宋湘、龚自珍等人,没有提到曾国藩,应是彼时对曾国藩的评价还未完全扭转的原因。2000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版虽然恢复了曾诗,但“前言”依旧用了1981年版。如钱先生能再重写“前言”,或许会加上曾国藩对黄遵宪的影响,如今这个影响倒少见有人揭出,颇可惋惜。
那么,《人境庐诗草笺注》建国后版本对1936年版除了上述删改外,是否还有别的删改?粗略地比对两个版本可以发现,在黄诗提及太平天国与义和团运动的笺注中,1957年及后来的版本对1936年版做出了较大更动,此事未见钱先生在2000年跋语中提及,兹举两例以明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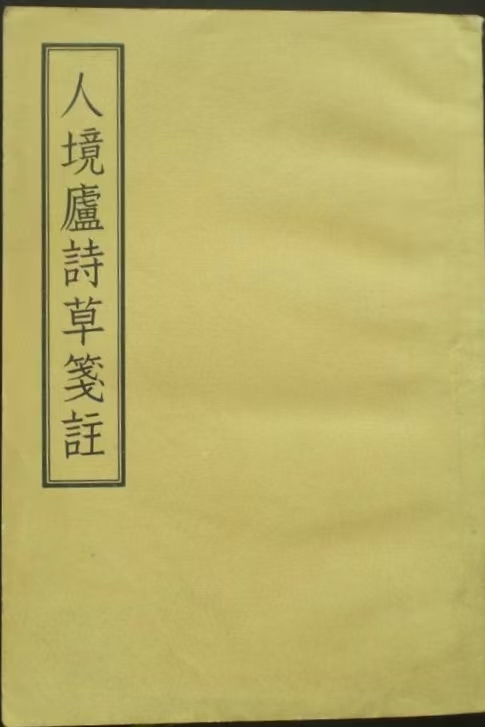
《人境庐诗草笺注》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卷一《乙丑十一月避乱大埔三河墟》,1936年版在诗题注引《清史稿·穆宗纪》云:“同治四年十一月庚辰,粤匪陷嘉应。”又在“尚有群蛙乱跳鸣”句下引《嘉应州志》:“同治三年甲子,官军克复金陵。发逆余党汪海洋、李世贤、丁大洋、林伯焘窜扰江闽粤三省边界,众号百万,所至辄陷城邑,州属之平远、长乐皆先后失守,镇平失守者凡三。”又引《国史·左宗棠传》:“十月海洋陷广东嘉应州,宗棠奏言:‘发逆仅一汪海洋而广东患,气在惠潮嘉三郡,海洋回窜,土匪散勇多附之。’”来笺释写作背景。1957年版题注,删去了《清史稿·穆宗纪》的表述,换成了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汪海洋传》:“乙丑十五年五月,入广东境,破清军于镇平,进攻嘉应州。八月,清将康国器来攻。镇平陷。海洋走平远。九月,趋江西。清军拒之。复由江西入广东,破平和,走连平。越山入兴宁。所过城邑,辄绕道疾趋。旬日间走数百里。十月,突袭嘉应州,克之。清军还救不及。左宗棠檄各路清军来围,嘉应州城环水,其南曰河南,海洋以重兵驻之。又南曰小密、曰芹菜洋,地皆险要,清军独缺围,不扎一营。海洋即由芹菜洋倾城出战,大败清军。宗棠急扼三河坝,三河者,大小靖溪及雁石溪所汇也,其地崇山絶涧,为潮州要冲。”又将“尚有群蛙乱跳鸣”句下注作了简化,删去了《国史·左宗棠传》的引述,《嘉应州志》中的引文也将“官军克复金陵。发逆余党”“州属之平远、长乐皆先后失守,镇平失守者凡三”数句删去。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的材料,较之原引几处描述该战役的文字更详细。但更重要的是,他是站在太平天国军队的立场上写作的,传统政治话语中将太平天国描述为“贼”“发逆”的表述被全数替换了。
再举一个黄诗提到义和团运动的例子。卷十《初闻京师义和团事感赋》,1936年版题注引《清史稿·德宗纪》:“光绪二十六年正月,拳匪起山东,号‘义和拳会’……夏四月庚寅,义和拳入京师。”末句“未知盗首定何谁”则引李希圣《庚子传信录》、罗惇曧《庚子国变记》中的相关内容,到了1957年版,题注引《清史稿·德宗纪》,仅“夏四月庚寅,义和拳入京师”一句。“未知盗首定何谁”句,则将李希圣《庚子传信录》和罗惇曧《庚子国变记》中的内容全部删去,换成了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义和团入京后,声势大张。清政府任命载勋、刚毅统率义和团,企图干涉团民行动。但重要事件,载勋等不能作主。仍请坛中大师兄焚表烧香,载勋等不能干预。”最后又加了一段“案”:“公度对义和团运动,采取仇视态度,称之为盗为匪,盖当时地主阶级、买办阶级、资产阶级对义和团都采取反对态度……历史条件与阶级立场使然。”与前举删改太平天国相关注文的方式如出一辙,将原引文献中站在清廷立场,有关义和团文字的负面表述删去,有些地方则换成了站在义和团立场上说话的、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中叙述的相关记载。最后甚至还加了一段案语,表明黄遵宪对义和团态度乃是“历史条件与阶级立场使然”。纵观1957年版《人境庐诗草笺注》中涉及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笺注的删改,大致方向都是一致的,即将原注中对太平天国称“发逆”、义和团称“拳匪”以及对二者污蔑的表述尽数删去,补充了大量站在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立场上说话的《太平天国史稿》《中国近代史》的相关内容。
那么,这种删改是如何形成的?依照2000年中国青年出版社跋语所言,该书在1957年由上海的古典文学出版社、198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多次重印”,诸序“俱被重印本删去,注中所引曾国藩日记及诗句亦被删去,其他笺注内容,颇多更易”,则似乎这些删改皆是应出版社的要求,而始作俑者就是重新出版该书的古典文学出版社。真实的情况确实如此吗?结合当时一些史料、档案,细绎该书出版的过程,似乎问题并非那么简单。
《夏承焘日记》1954年7月26日载:“发新文艺出版社片,介绍钱仲联《人境庐诗笺注》。”可知《人境庐诗草笺注》在建国后,曾由夏承焘先生介绍给古典文学出版社前身,也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的新文艺出版社古典组。但夏先生日记1954年9月9日又说:“接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函……谓仲联《人境庐诗笺》正征求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意。”则《人境庐诗草笺注》的稿件,又曾到过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1954年,除了新文艺出版社与夏承焘先生接洽外,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在稍后向夏先生约过稿,并询问长远的选题计划(具体可参看拙作《夏承焘〈姜白石词编年笺校〉出版的前情》,载《书城》2025年5月)。应是在当时,夏先生除了透露自己的研究计划外,也向他们介绍了几部其他人的古典文学著作,包括《人境庐诗草笺注》。雅昌艺术网“2019年春季书刊资料文物拍卖会(一)”之拍品信息,有1954年钱仲联致夏承焘函,正及《人境庐诗草笺注》事,其中说到:“近示所称去函北京人民出版社接洽一节,未知是否新文艺出版社旧事?如系两回事,自以交人民出版社为佳。诗笺已于上月向友人处取回,当遵照古籍刊行社意见细加修正。”文中所云“古籍刊行社”即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54年成立的一个专门刊行文学古籍的副牌,由该信亦可佐证《人境庐诗草笺注》由夏承焘分别介绍给过上海的新文艺出版社与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而钱仲联先生选择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该书最初的出版机构。
1954年12月18日夏承焘日记:“得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复函……并言《人境庐诗笺》事,即函告仲联。”1954年12月25日:“得仲联复,谓《人境庐诗笺注》明春可改成。”则《人境庐诗草笺注》在1954年底,已经投往人民文学出版社,并由对方审稿。1955年1月17日,夏承焘又“得文学古籍刊行社函”,“言《人境庐诗笺》观点多问题”,当即“作仲联复,属其改《人境庐诗笺》关于义和团等处之观点,先改成一册寄社,请提意见”,1955年1月21日,“得钱仲联函,谓《人境庐诗笺注》月内可整理完毕”。可知人民文学出版社在看了《人境庐诗草笺注》后,觉得钱仲联在对义和团等处问题上,“观点多问题”,夏承焘自然也不敢怠慢,马上寄书劝他进行修改。1957年改稿上对太平天国、义和团等问题的诸多删改,应该就是1954、1955年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审稿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的。
但此后,《人境庐诗草笺注》的出版似遇到了一些困难。夏先生1955年3月30日日记载:“(徐)步奎告予新文艺出版社有友人来函,怪予介绍龙、钱二人印书。”将龙榆生、钱仲联二人并举,应该是二人在建国后曾因历史问题遭到非议。1955年7月16日,夏先生又记录了他写“检查书”的情况,说主要写了两点,其中一点就是“对人只片面注重其学问业务,而忽略其政治思想”,举的例子正是“介钱仲联《人境庐诗笺注》”。《人境庐诗草笺注》本来就被人民文学出版社认为“观点多问题”,钱仲联先生的“历史问题”又被揭出,该书的出版形势,陡然变得严峻了起来。
不过,夏先生并未因钱先生的“历史问题”而疏远他,对《人境庐诗草笺注》的出版还是心心念念。1956年7、8月间,夏先生入京参加教育部召开的中国文学、历史教学大纲会议,在与时任教育部副部长柳湜会面时,专门谈了钱仲联的问题。1956年8月17日日记载:“与柳湜部长说钱仲联事,案间适有《人境庐诗笺》也。”也许当时对钱仲联先生著作出版的情况开始有些松动,与柳湜的会谈,应该是得到了《人境庐诗草笺注》可以出版的肯定答复,8月22日,夏先生回到杭州,“即作仲联复,寄来《人境庐诗草笺注》改稿三册”。8月25日,“晨寄出钱仲联《人境庐诗笺》及《清诗选》稿五册与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1月3日,“得仲联扬州函,谓《人境庐诗笺》及《昌黎诗笺》古典文学出版社皆已承印”。《人境庐诗草笺注》的出版事宜终于尘埃落定,由刚刚从新文艺出版社古典组改组而来的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即《人境庐诗草笺注》最早由钱仲联决定,选择投往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何在其出版遭到阻滞中辍,继而再次启动后,直接寄给了古典文学出版社?这应该与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著作出版出现问题有关。夏承焘1956年8月18日日记载:“江津王利器君来,为作家出版社征稿。谓彼社为印中小学教科书,古典书出版困难,三年内不易解决。”夏承焘先生在京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王利器会谈时,王利器透露了作家出版社(即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亦是当时的一个副牌)“古典书出版困难”的事实,夏承焘先生当时的《姜白石词编年笺校》原本也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后便改投古典文学出版社(“古典书出版困难”或许也与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二编辑室主任聂绀弩与副总编王任叔之间的矛盾与斗争有关,亦可参见拙作《夏承焘〈姜白石词编年笺校〉出版的前情》)。彼时古典文学出版社刚从新文艺出版社古典组分出,正需古典文学的稿件,在这样的背景下,将《人境庐诗草笺注》直接寄给古典文学出版社也是非常明智和正确的选择。
《人境庐诗草笺注》出版的来龙去脉,大致已可厘清:即最早由夏承焘先生向新文艺出版社古典组及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别介绍,钱仲联先生最初选择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但人民文学出版社认为该稿对义和团等问题“观点多问题”,夏承焘先生向钱先生建议修改。后来,钱先生因“历史问题”,出版著作一度变得困难,形势变化后,才又将稿件投往已经由新文艺出版社古典组改组而成的古典文学出版社,最终顺利出版。稿件的删改,应该是接受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意见后即开始。那么,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意见,到底使钱仲联先生删改了多少?古典文学出版社审读后的意见又是什么样的?翻阅上海古籍出版社社藏《人境庐诗草笺注》之档案,大致可以解决这一疑问,下面将略加申说。
《人境庐诗草笺注》档案中有“新文艺出版社来稿处理单”一张,来稿日期为“1956年8月28日”,来源“夏承焘介绍”,应即夏承焘先生在1956年8月25日寄出的稿件。“编辑室主任意见”栏,填写有署名钱伯城10月18日的意见“李社长批示发稿”,后又附钱仲联1956年9月10日信件一封:
新文艺出版社总编室通联组负责同志:
前奉编通古(56)字第5176号来函,嘱将“人境庐诗”删去的部分,补笺寄上,现在已整理就绪,共21页,外加目录正误一页,一起挂号寄奉,即请分别插入注稿中以成完璧。
此致
敬礼!
钱仲联
九月十日
由此可知,古典文学出版社在收到稿件后立即开始了审读工作,之后便向钱仲联先生提出了审读意见,在钱仲联先生根据审读意见修改完毕后,就由社长李俊民亲自批示发稿。十分奇怪的是,从钱仲联先生的回信看,审读意见并非让他删去什么违碍的地方,而是将某些原来删去的地方补足。这又是怎么回事?档案中另附1957年10月15日钱仲联先生因沈曾植《海日楼集》整理与出版社编辑杨友仁先生的商榷信件中透露出删除、恢复的个中消息,其中说到:
“人境庐诗草”中反对太平天国、反对义和团之诗,弟稿中原已删去,后来古典出版社意见不应删去,嘱弟补足。
原来钱仲联先生最初投到古典文学出版社的、接受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意见的《人境庐诗草笺注》改稿,是干脆将其中反对太平天国、反对义和团运动的诗歌全部删去的版本。而古典文学出版社反而是认为这种删改违反古籍整理反映古人古书原貌的准则,又让他补足。钱先生补足时,自然不会将“丑化”“污蔑”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的注释再次出现,于是将这些注释换成了更为“进步”的版本。
现在看来,钱仲联先生的这种删去作品原文的做法有些太过“正确”,甚至违背了我们现在整理古籍的基本原则,如无古典文学出版社的意见,《人境庐诗草笺注》的学术价值恐怕将大打折扣。但当时正处于新时代与旧时代交替的时期,对文化遗产的继承与出版,到底持何种态度、用何种手段,都是可以讨论与商榷的。整理古籍,到底可不可以删改,也在可讨论的范畴内。1956年11月28日,上海《文汇报》第二版曾登载过一篇短文,题目是“古典文学作品能不能删改——上海出版界正热烈讨论”,文章不长,为让读者更清晰地明白当时对古典文学作品如何出版的态度,遂全文迻录于下:
上海出版界最近对古典文学作品重印时应否删节、如何删节等问题展开讨论。有些人主张把古典文学原封不动的出版;大多数人则认为古典文学的读者对象是广大人民群众,不是专给研究者用的,因此有必要将古典文学中的糟粕部分删去。
主张把古典文学原封不动出版的人认为:古典文学是祖国的文学遗产,改动了就会破坏原著的精神面貌、结构和风格;应当保留古典文学原著的面貌,反映当时的封建社会的真实情况,否则不能使读者通过作品去认识那个时代生活的复杂面貌。有人建议出版古典文学作品不应删改,但要另写序文指出其糟粕。
主张删改人的意见是:将古典文学中的糟粕部分删去,对读者是有利的。改写古典文学作品,用现代汉语翻译,对读者方便,但必须在尊重古代人劳动的前提下,在丰富、提高、纯化古典文学的基础上进行删改。删改也只限于删掉一些反动的、荒诞不经的、淫秽的、侮辱劳动人民的内容,一般封建迷信的可不必删改。也有一些人主张采用节选本,如开明书店以前出版的“水浒”版本,或者是以某一人物和某一事件为中心的节选,如“诸葛亮”“赤壁之战”的故事等。还有一些人则认为有些作品需要加以彻底的改编。正在展开的这个讨论,已引起出版社的编者、读者和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的强烈兴趣。
可知在当时的背景下,古籍整理删或不删都是有道理、有商榷余地的。幸运的是,从今天看,建国后古典作品的出版还是以忠实反映“原著的精神面貌、结构和风格”为主,现在这也已经成为整理古籍的学术共识。这一局面的达成,与当时有识的古籍出版者做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史研究[23&ZD21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文中“雅昌艺术网”所载钱仲联致夏承焘信、《文汇报》1956年11月28日文,皆承友人宋希於先生告,特此感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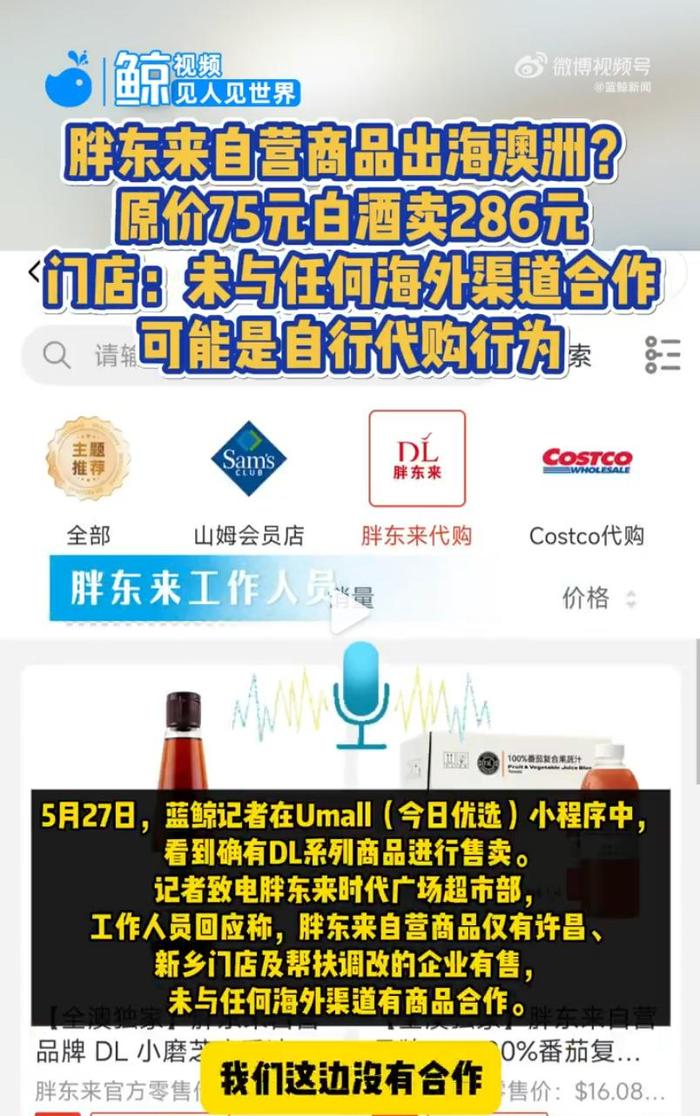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