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弗雷德·布伦德尔(Alfred Brendel,1931年1月5日-2025年6月17日)竭尽全力让自己看似平常。身材高挑的他在与人见面时会弯腰躬背,努力接近其他人的身高。他的西服总是无法合身。他的领带是深色的,没有花纹。他唯一引人注目的配饰是一副黑框眼镜,类似迈克尔·凯恩(Michael Caine)在《伊普克雷斯档案》(The Ipcress File)中戴的那种——但此二人之间并无可比之处。凯恩身形灵活、气场性感、言简意赅,而布伦德尔走入房间时步态踉跄,谈吐漫无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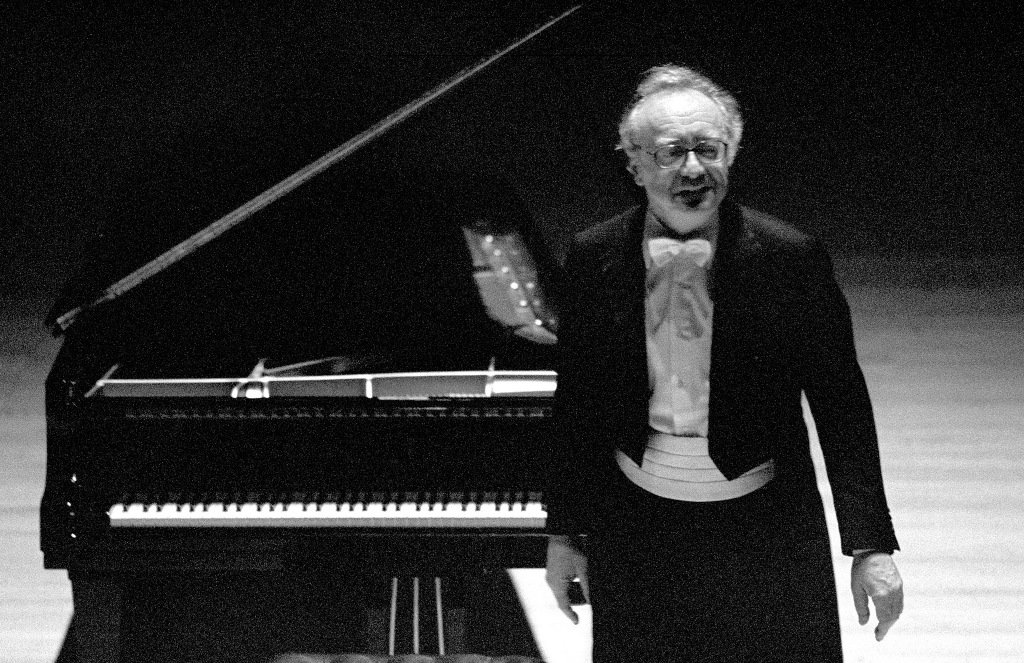
阿尔弗雷德·布伦德尔
出版商乔治·韦登菲尔德(George Weidenfeld)曾经鼓励他写本自传。布伦德尔拒绝了。“我觉得自己没什么意思。”他曾这么说。对住在汉普斯特德路两边的精神分析学家们而言,这种说法使这个人不仅仅是有趣而已。他们会说此人一定是在自我否认。我们这个时代最多产的钢琴家就像一本有着七个封印的书,每个封印都完好无损。
他的童年辗转于捷克、克罗地亚和奥地利各地。他曾穿过格拉茨的阿道夫·希特勒广场去找钢琴老师。他从未上过专业音乐学校。他在维也纳也是个局外人,口音不太标准。他曾坦言,“我没有根基,我很高兴不需要任何土壤。”
1951年,一位不那么光明正大的制作人乔治·德·门德尔松-巴托尔迪(George de Mendelssohn-Bartholdy)请布伦德尔录制了弗兰茨·李斯特的《圣诞组曲》。紧随而来的是在一家不起眼的美国唱片公司Vox-Turnabout发行的穆索尔斯基《图画展览会》和巴拉基列夫《伊斯拉美》这些华丽的斯拉夫音乐。最终,他升级获得了与维也纳爱乐乐团录制莫扎特协奏曲的机会,那时乐团使用“Pro Musica”这个假名来规避他们当时的合同限制。来自奥地利的全能指挥家赫伯特·冯·卡拉扬只与布伦德尔合作过一次——恩斯特·克热内克的一部协奏曲,显然对他不屑一顾,并拒绝邀请他去萨尔茨堡。
布伦德尔在Vox唱片公司深耕贝多芬,在那里录制了32首奏鸣曲,还有一些变奏小曲儿——《天佑吾王》《统治吧,不列颠尼亚!》——只是玩笑性质的模仿。不知何故,他总能表现得既严肃得要死,又丝毫不正经。
1970年时,一场在伦敦伊丽莎白女王音乐厅举行的贝多芬作品独奏会改变了一切。第二天早上,三大唱片公司代表冲进酒店敲响了他的房门(过去我也见过这种情况,并不是啥好看的景象)。飞利浦唱片公司凭借一份录制维也纳作曲大师名作的计划最终得标——海顿、莫扎特、贝多芬,尤其是舒伯特,其钢琴成就一直被其他作品所掩盖。他们想出了一个策略,将布伦德尔定位成一位值得听众信赖的钢琴家,其准确性凌驾演奏者的自我。在布伦德尔的录音中,每个音符都恰到好处,每个力度都与乐谱相符。他的演奏会座无虚席,观众们是为了学习知识,而不是娱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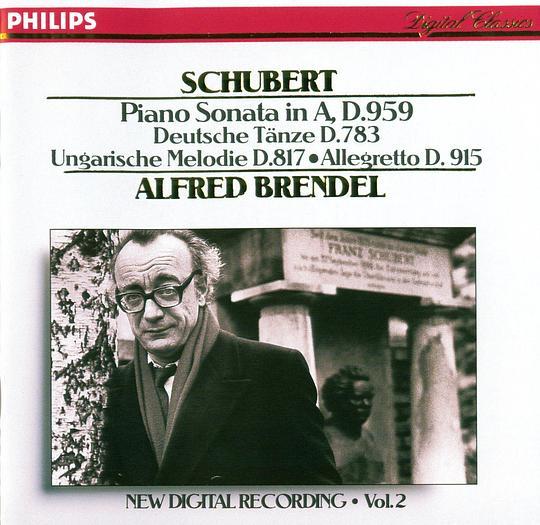
布伦德尔演奏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专辑封面
布伦德尔自述他获得了“相当怪诞”的成功。美国人对此感到困惑:成功有什么不好?《纽约时报》为“无聊”塑造了新的同义词,对钢琴家极有发言权的哈罗德·勋伯格认为他“勤勉、死板,缺乏想象力”。布伦德尔曾说:“我对作曲家负责,尤其对作品负责。”
他在舞台之外培养了一种古怪的智慧和亲切的社交能力。有一次我跟他还有梅纽因夫妇共进晚餐,他严厉批评我登在《每日电讯报》上的一篇轻浮的文章,把钢琴家分为书呆子或疯子、知识分子或狂人。他怒气冲冲地说:“你把我归类成书呆子,而我显然是个疯子。”这又是自我否认吗?
个人形象很重要。飞利浦唱片公司等布伦德尔批准最新的唱片封面照片,要等上几周甚至几个月,而这些照片看起来和他们之前出版的所有照片一模一样。他的唱片封套的色彩是棕色上再加棕色,就像泥土一样。你买布伦德尔的唱片是因为你真的需要,而不是因为它吸引你。
他做事一丝不苟,会在音乐会前花一上午来测试四架音色一模一样的斯坦威钢琴,但到演出结束后才承认自己选错了。他偶尔会突然承认自己焦虑不安。我曾指出勃拉姆斯某部协奏曲中一个“困难”的乐段。“永远别用那个词,一旦我开始觉得它困难,我就再也弹不动这首曲子了。”他这么斥责我。
当他不坐在琴凳上的时候,他会去美术馆、剧院、电影院,他对各种文化有着广泛的兴趣,渴望去认识各种文明。他在工作室里摆满了非洲艺术品。他用英语讲授歌德,还写过一篇关于“迷人”的达达主义者的颇为旁征博引的论文,尽管达达主义者其实都是些狂人。他把来他家做客的流亡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介绍给了汉普斯特德的邻居、英国间谍小说家约翰·勒卡雷。为了健康他会去野外散步,回家的路上会再买一块黏糊糊的蛋糕。像济慈、柯勒律治和乔治·奥威尔一样,衣摆飘扬的布伦德尔也是汉普斯特德的典型人物,然而他直到去世都一直保留着奥地利本色。
六十多岁时他就早早退休,显然如释重负。2008年圣诞节前一周,他在曾经上百次登台的维也纳金色大厅,最后一次面对观众合上了键盘盖。他曾计划写下更多的诗歌和文章,总有年轻的音乐家渴望他分享一丝智慧,也总有听众渴望听他讲述他曾攀登的音乐高峰。
这段音乐旅程从巴赫一直延伸到阿班·贝尔格,是一条几乎没有岔路的直线。他厌恶柴可夫斯基和拉赫玛尼诺夫,鄙视德彪西和拉威尔,只被肖邦吸引过一次。他的巅峰是阿诺德·勋伯格笔下狂暴的钢琴协奏曲,他曾经录制过四次,以及费卢西奥·布索尼那令人绞尽脑汁的《对位幻想曲》。
他将一种特殊的共鸣保留给舒曼——从钢琴协奏曲到包括《童年情景》那样的小品,尽管他本人拒绝回顾过往。阿尔弗雷德·布伦德尔小心翼翼回避危险的岸边,罗伯特·舒曼曾在那里大胆漫步。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