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改编自马伯庸原著同名小说《长安的荔枝》电影版提档热映。月前,35集电视剧版播出后,部分观众认为剧情拖沓严重,堪比“用99道工序端上来一盘拍黄瓜”。电影版《长安的荔枝》能否实现后发制人,引人注目。

《长安的荔枝》电影海报
情节上做减法,人设上做加法
故事讲述了上林署小官李善德被迫接下从岭南转运荔枝到长安的“不可能任务”,在千辛万苦完成转运项目后却被全家流放岭南。相较于剧版,影版删繁去芜做了减法,使人物立场更加简明。开场二十分钟,屏幕上开始了贵妃庆生的倒计时天数。时长稍过半,李善德已初次从岭南回到了长安,为后面的重头戏留足头寸。剧情时长安排停匀合度,遵循好莱坞商业片经典的三幕式叙事节奏。

荔枝转运的始作俑者内宦鱼朝恩
相较于原著对人物关系的真实刻画,电影对人物做了更加脸谱化的直白处理,让小人物的互帮互助成为存在主义难题的终极解法。在皇权、官权、父权的合围下,小人物各有各的难处,但在互帮互助、通力合作的努力中,小人物们找到了各自的出路。众志成城的人心所向,甚至足以颠覆锦绣长安,深化了故事的存在主义议题。这也为李善德最后铤而走险的摊牌埋下了伏笔,让人物的转变更加合理。
最大看点:如何用视听语言表现原著主题

用扇形构图表现向心收摄的权力结构
影片多处运用了环绕镜头来表现主人公深陷困境却无力超脱的窘态。上林署请君入瓮的酒宴、荔枝园遭到破坏性砍伐的群戏,都体现了李善德天旋地转的无力感。向中心进行收摄的半圆形构图被反复用来表现权力的向心结构。鱼朝恩莅临上林署时,官员跪成了一圈,千佛阁中右相和李善德形成对峙,亦呈环状,这种“全景敞视”的半圆形构造正是权力得以展开规训并获取最大化效益的视角呈现。
影片对光影的运用独具匠心。前期的李善德在署地郁郁不得志,导演多以从狭长幽细的窗格中透出来的一丝光亮作为侧光,营造府衙沉重压抑的整体氛围,烘托各怀鬼胎的人物心理。等到李善德挂上银牌奉了旨令回署之后,已然变成了钮祜禄·善德——站在台上发号施令,来自全开间的纯然阳光已将暗影一扫而空,光影的转换暗合了他从忍气吞声到扬眉吐气。

李善德独自一人对抗国家机器的光影对比
在影片接近尾声处,李善德独自骑一白马从长安的黑色寂夜中脱颖而出,一路经过灯火通明的长街,尽头的红色宫门缓缓打开,强光过后,荔枝出现在画面中心,内宦层层环绕,舞姬妖娆娇嗔,满目奢华不似人间,这和先前的紧张激烈形成了鲜明对比。“何不食荔枝”的奢靡和“一骑红尘”的悲哀,在光与影的更替中被衬托得无以复加。

“一骑红尘”的视觉化具象
“荔枝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电影在声色方面充分调动起观影者的感官刺激。各部官员鱼贯而来身着青绿绯紫、新鲜荔枝的红壳白肉被布鞋反复践踏碾压、宛若红焰的木棉花四处纷飞、大红色的金鱼壁画宛若游龙,此是色。阿僮问:“这皇帝就非要吃岭南的新鲜荔枝不可?”苏谅答道:“这荔枝,味中有江山,味中有美人。”此是味。荔枝的味道“就那么回事”,但荔枝带来的通感,是阿僮被头人父母宠溺养大的天伦之乐,是小人物为之付出身家性命的催命符,甚至是锦绣长安背后一颗隐秘的毒疮,快要淌出黑色的腐蚀性汁液,此是依于色与味转引而来的法。李善德买下新宅的锣声清脆、从岭南出发时的胡笳悲鸣、孤身入长安时的鼓声咚咚和人声吟唱、内廷上苑的歌舞升平莺歌燕语,带来丰富的听觉层次,此是声。
人的感官所系不过就是色、声、香、味、触而已,加上意根所摄的法则成六识,六识又可以开合为五蕴。当内宦鱼朝恩当众宣布皇帝赏赐新鲜绿李一篮,本已抱着必死觉悟的李善德从地上踉跄起身,而一旁的杨国忠堪堪停下手中的毛笔,正在抄录的《心经》断在了“照见五蕴皆空”一节,表明即便身居高位,也难免五蕴炽盛之苦。影版《长安的荔枝》极尽声色腾挪之能事,把存在者的困境彻底地暴露在观众面前。
神佛灭度、人畜混杂的苦难世界是否适配喜剧tag
初到岭南,李善德为边远之地的异域情调所震撼。牵在手艺人绳上的猿猴、披着彩色挂布的大象、笼中的硕大鸵鸟、何节帅豢养的黑熊,除了增添喜剧风味之外,也彰显了岭南边地之人原始的兽性本能。阿僮被人唤作獠女,钻进荔枝园中上下翻飞如鱼得水。林邑奴人猿泰山式的经典动作戏,展现了他的原始本能。边地人畜混居,但原始简单的兽性在人心感化之下,也渐渐接近并展露出崇高的人性光辉。

荔枝园中上下翻飞的侗女阿僮
上位者不仁、以庶民为刍狗的冷酷,则是通过虚无缥缈的神佛之性得以体现。在招福寺巨大鎏金坐佛的掩映之下,杨国忠粉墨登场,佛像低眉俯视芸芸众生,面上无悲无喜,是为无情之征。

巨型佛像俯瞰芸芸众生
在千佛阁中,杨国忠挥起手中的鎏金禅杖连续击打,李善德的额头瞬间流下几道血痕。众生本具如来清净自性,杨国忠在挥动禅杖的那一刻,即犯下了“出佛身血”的无间恶业,注定了堕入地狱的结局。李善德一直惦记着妻子要木棉花的“小事儿”,这包爱的木棉为他挡下了刺客的致命一刀。善恶随人,福自己招,在虚无缥缈的宏大叙事和日常生活的平凡细碎之中,李善德始终选择的都是将心比心的人性而非不可捉摸的神性,最终也使他塞翁失马般地躲过了长安沦陷的危机。
也正因为李善德丰沛流动的人性,他虽然逃过了长安,却没能逃过荔枝树下的那场痛哭。他哭的不是那从来没有属于过他的浮华长安,而是他上班早高峰路过的烤馍摊、肉包铺子,是七嘴八舌热心招呼的左邻右舍,是鳞次栉比酒坊林立的热闹市井,是酒酣微醺胡姬劝客的一支胡旋舞,以及万家灯火平安度日的阖家欢好。长安的色、声、香、味、触,在普通人李善德的体验中一直都是如此具象化,于是才有了尾声处的千红一哭,万民同悲。神佛灭度之后,源于世俗又超越世俗的人性价值才是人类存在的根本意义。

初到长安的少年李善德
不少观众表示,《长安的荔枝》在宣发时似乎错误地添加了“喜剧”的tag,导致观影期望有所落空。鲁迅先生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就说过:“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悲喜剧只是不同的表现形式,两者自毁性的内涵本就别无二致。从岭南千辛万苦转运荔枝到长安,多少人为之出生入死,上位者却苑中犹歌舞,这难道还不够荒诞吗?一国之相本应为民做官,功在社稷,却重税厚敛,到头来不如一个九品小官心怀天下,这难道还不够错位吗?喜剧的内核是悲剧,诚然。
《长安的荔枝》也注定不可能成为令人捧腹大笑的爆米花喜剧片。故事的出发点先验地决定了它不可能是爽剧,李善德不可能上演小人物的成功逆袭。转运荔枝一事建立在生灵涂炭、万骨齐哀的巨大牺牲之上。对李善德而言,生存和伦理的两难困境注定是无解的。观众体认到的憋屈心酸的观影体验,恰好反映了制作团队在视听策略上的成功。李善德式的人物迫使观众直面自身的困境,重温避无可避的真实瞬间,在道心叩问中忆念初衷,尽管掺杂着认输认怂认命的无奈,但只要有光有爱有人世间的温暖,就可以走得更远,无愧于天地间。
(常方舟,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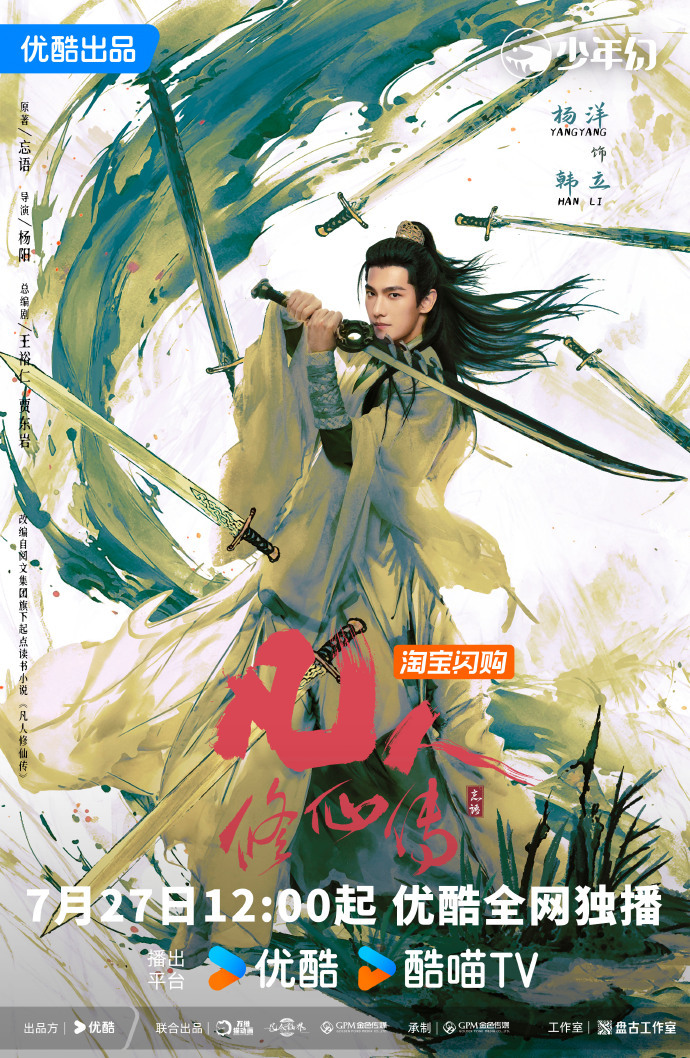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