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空公司“杀熟”背后
在达美航空(Delta)的带领下,许多航空公司现在正在与人工智能公司合作,利用大数据进行价格设定。借助新的监控技术,这些公司利用消费者隐私设定“个性化”票价,从而抬高票价。中文社交媒体上经常有对“杀熟”的讨论,人们发现在航空公司或代理平台上多次搜索后价格提高,晒出不同账户得到的不同价格,但机票定价背后的机制比这更复杂。屡获殊荣的独立调查新闻编辑室Lever的一篇文章(作者Katya Schwenk和Luke Goldstein)介绍了这种“监控定价”。

当地时间2025年7月27日,美国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罗纳德·里根华盛顿国家机场,工作人员在美国航空的一架飞机旁。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Lina Khan讲了一个航空票价的例子,体现了新一代监控定价的危害。“假设你查看了一张飞往某地参加家庭婚礼的机票。该航空公司利用你设备上的定位数据,推断出你的家乡;再结合你在社交媒体上的发布内容,发现你计划旅行的时间,以及你搜索新餐厅或活动的记录——这些信息可能会让它们推断出你在准备婚礼相关的事情。”然后,航空公司可以用AI算法将这些数据转化为价格策略——对婚礼日期周围的航班提高价格,因为它知道你别无选择只能出行。
在达美航空因扩大使用人工智能为乘客设定票价而面临公众反对之后,该公司近日向联邦立法者致信,否认其使用“个性化定价”来哄抬消费者价格。但许多航空公司(以达美为首)正与人工智能咨询公司合作,这些公司吹嘘其“超个性化(hyper personalized)”定价能力。这套新的机票定价体系是航空业长期以来基于大数据的定价实验的一部分,为全经济范围内的“监控定价”奠定了基础,这种定价模式利用消费者隐私来制定“个性化”价格。
现在,通过共享算法,航空公司的人工智能业务还可能导致非法的合谋,从而威胁到所有人的机票价格上涨,这是与Lever对话的专家所警告的。
个性化定价利用监控技术和数据收集,根据每位顾客的个人信息为其设定个别价格。AI工具可以筛选大量关于客户或竞争对手的数据,分析趋势,从而生成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价格建议。
在上个月的一次财报电话会议上,达美航空总裁Glen Hauenstein向投资者谈到其AI定价时说:“我们对看到的情况感到满意……并且我们将继续推广。”他宣布,到今年年底,该航空公司计划用AI工具设定20%的国内票价。这一宣布引发了联邦立法者的反对、旅客的愤怒,甚至竞争航空公司的谴责。作为回应,达美现在声称,它不会利用与AI的合作来根据消费者独特的个人和行为数据设定个性化价格。
但为其提供AI系统的公司(一家名为Fetcherr的以色列初创企业)在一篇现已删除的博客文章中,曾夸耀自己向消费者提供“超个性化”价格。根据彭博社首次报道的一份2024年白皮书,该初创企业与一家未具名的大型航空公司合作进行试点项目时,Fetcherr的联合创始人提出了一套复杂的定价策略,这些策略“超出了人类认知的极限”来增加收入,就连创始人自己也承认,这可能被视为“剥削”。
Fetcherr属于一个航空定价顾问的细分行业,这类顾问与大型航空公司签署协议。Fetcherr声称能为客户增加4%–6%的收入。其客户包括至少八家航空公司,并已与达美签署合作协议。达美高管此前表示,他们预计Fetcherr定价策略将在业内变得普遍:“随着时间推移,我们的竞争对手都会有这个。”
正如前联邦贸易委员会主任Samuel Levine上周在国会听证会上作证时所说,Fetcherr是“从市场竞争向算法寻租(algorithmic rent-seeking)转变”这一趋势的体现。在这种趋势中,行业内的公司使用第三方定价平台来统一价格,这种做法往往类似于高管之间的老式串通。
在房地产行业,算法定价平台RealPage被指控帮助房东操纵租金价格。一个类似的案件正在法院审理,涉及一家名为Agri Stats的农业定价服务,政府指控其帮助肉类加工商操纵价格。
进步派智库Groundwork Collaborative执行主任Lindsay Owens指出,如果多家航空公司使用相同的生成式AI定价平台,而票价出现趋同现象,就可能出现算法合谋的情形,“价格很可能在不同航空公司之间同步上涨”。
如今,动态定价通常与Uber这样的网约车平台联系在一起,该平台使用算法在高峰“加价”时段提高价格。但这种定价方式最早是由航空公司首创的——当某一航班的机票开始迅速售罄时,剩余座位的价格会被提高,这意味着乘客为同一航班支付的价格可能相差巨大,这种做法有时被称为“价格歧视(price discrimination)”。
AI定价是航空业长期探索利润最大化手段的延续。早在1980年代,航空公司就建立了专门的收益管理部门,研究乘客的最高可接受价格,进而衍生出行李费、选座费等附加收费。
动态定价策略最早由航空公司开创,即当航班售票接近满员时,剩余座位的价格会急剧上涨。节假日前的热门航线票价甚至可能飙升至平时的五倍。
互联网兴起后,在线旅游平台(如Expedia)通过追踪用户浏览记录、位置等隐私信息来推送定制价格。与此同时,“滴灌式定价”(drip pricing)让比价变得困难——购票过程中附加的座位、行李等额外费用被隐藏到最后一步才出现。
如今,动态定价、个性化定价和滴灌式定价共同奠定了“监控定价”的基础——利用个人与行为数据,从每位乘客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金钱。
Fetcherr总部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根据其网站介绍,该公司由以色列国防军的前情报和网络部门成员创立,并得到了以色列创新局(Israel Innovation Authority)的资金支持,后者是一个政府机构,负责推动以色列的科技发展。根据以色列政府网站的声明,以色列创新局与Fetcherr合作,资助了一个旨在“推动旅游业数字化转型”的项目。
一些隐私倡导者表示,这种军事情报背景与商业定价算法的结合令人担忧。“这类背景的人员往往在数据收集、行为预测和模式识别方面拥有很高的专业能力。”国际数字权利组织AccessNow的资深政策分析师Natalia Krapiva说,“当这些技能被用于最大化企业利润时,它可能会变成一种剥削工具。”
Owens警告说,如果达美航空与Fetcherr的合作证明成功,其他航空公司很可能会迅速效仿。“当一家大型航空公司找到了新的赚钱方法,整个行业往往会跟进。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这些策略会从航空业扩散到酒店、娱乐票务,甚至医疗领域。”她指出,动态定价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最初是航空公司的专利,如今已被广泛用于演唱会门票、体育赛事,甚至主题公园。
如果AI驱动的监控定价变成主流,会加剧美国消费者已经感受到的生活成本压力。她认为:“人们已经被迫为住房、医疗和食品支付创纪录的高价,如果机票也进入这种模式,将进一步削弱家庭预算。”
目前,美国几乎没有明确的法律来限制航空公司使用AI或大数据进行价格设定。
Krapiva说:“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这类工具将会迅速扩散到整个经济。到那时,不只是机票——从你的杂货账单到看医生的费用,都可能由监控驱动的算法来决定价格。”
作家和活动家Cory Doctorow在自己的Medium页面发表文章评论了此类AI价格剥削。
他声称,数据经纪商手中掌握着各种关于你的信息——包括你开车去过的所有地方、你手机和耳机蓝牙信号经过的每个位置、你买过的所有东西、访问过的网站、做过的搜索记录,甚至还包括通过手机间谍软件直接窃取的数据。所有这些信息可以被整合成一个你无权查看、更无权修改的文件。拜登政府曾试图通过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禁止这种做法,但该规定被特朗普非法废除。
企业已经找到了无数利用这些数据牟利的方法,其中之一就是监控定价。例如,一些为护士提供工作的打车式应用,会用监控数据判断哪些护士债务缠身,然后给她们开出更低的时薪,因为这些人更难拒绝低价工作。
与此类似,监控定价系统会根据你个人的支付能力来调整价格——这意味着相同的商品,你可能比别人付出更多钱,也就是说你的美元价值比别人的美元更低。
作者称,航空公司监控定价的做法与Uber的策略如出一辙:Uber既会根据司机的行为调整劳动报酬,也会根据乘客的支付意愿调整车费,从而把钱从司机和乘客手里转移到股东手里。今年6月,《卫报》报道了哥伦比亚商学院的一项研究,指出Uber的“动态定价”系统导致司机收入下降,而公司利润却大幅上升。该研究发现,Uber的“算法定价歧视”提高了乘客费用,并系统性地降低了司机收入。
不过,打车是临时的小额消费,用户很少比价;而机票通常提前购买,且在线旅行网站会显示多家航司的报价。为了绕过这种比价机制,英国航空最近大幅调整了常旅客奖励制度——如果不是在自家网站购票,旅客几乎无法获得有意义的积分。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阻止乘客通过第三方平台寻找更低票价,同时为引入监控定价扫清障碍。
与Uber不同的是,Uber极力隐瞒自己在搞监控定价,而达美却高调发新闻稿。这种做法受到某些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吹捧,他们声称这会提高市场效率,让那些买不起高价的顾客得到折扣。但现实是,卖方并不想增加“信息透明度”,他们只是想监视你。一旦有人试图反向监控他们(如爬取价格数据以寻找低价),企业往往会用诉讼威胁加以打压。
更荒谬的是,这让作者想起了AI行业的一大骗局——所谓的“自主代理AI”。厂商声称不久后你可以让聊天机器人替你跨网站比价并购票。但这几乎不可能实现,因为各大网站不仅没有统一的可读接口,反而处处设置障碍来阻止这种比价行为。这就像自动驾驶汽车的骗局一样:一开始声称能应对复杂人类环境,后来却要求人类改变行为去适应机器人。
总之,自动化确实能带来好处,但监控定价这种模式没有任何社会价值。它唯一的作用,是在乘客和消费者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把更多财富转移给企业股东。
抄袭与创作的区别正在消失
输入提示词然后将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的内容占为己有,这是一种抄袭吗?美国作家、记者奧利佛·巴特曼(Oliver Bateman)在其Substack博客发表了“抄袭与出卖”( The Work of Plagiarism and the Work of Selling Out)一文,指出随着创造、拿取、售卖创意的整体机制的变化,我们正在目睹创作和抄袭之间的最后区别逐渐消失。
巴特曼指出,“出卖”曾经是X时代经常使用的道德指控。从垃圾摇滚乐队签约厂牌,到独立导演拍广告,再到先锋作家写畅销书和在企业就职,都会被指责为出卖行为。这种指控建立在原真性的艺术表达和商业妥协之间存在一条清晰的界线。后来,社交媒体将每一个人变成了自己的营销部门:领英档案、Instagram版面,推特品牌……现在,每个人都在兜售一些什么。而当所有人都在做销售的时候,与出卖对立的那个外部就不复存在了,对于出卖的指控自然也就不再有意义。
文章指出,这也是抄袭正在经历的进程,比出卖要慢一些,但人工智能即将完成这项工作。
使用人工智能写作的人做的事情实际上是这样的:他们输入提示,或许再贴一点背景材料,然后按回车键,然后复制跳出来的任何内容。大多数人甚至不会浏览输入的内容,更别说检查输出的内容是否合理了。他们肯定不会思考这些文字最初是从哪里来的。这台机器拥有海量的有版权争议的文本的访问权限,吐出的是看似合理的平均值。巴特曼认为,每一个这样生产出来的人工智能段落都可以被公正中立地描述为抄袭。
巴特曼写到,他过去在大学教书批改学生论文时,可能每个学期会抓到一个明显的抄袭者,通常是某个来自某个反抄袭意识较弱的教育体系的国际学生在谷歌搜索结果中复制粘贴。现在,大学老师们正在被人工智能论文淹没,不仅是懒惰的学生,还有律师、数据科学家、医生,他们都在把提示输入抄袭机器然后将输出当成自己的。
然而,人工智能并不是抄袭的始作俑者,人类抄袭也没有全然销声匿迹。巴特曼提到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有人把一篇其他人写的关于“压缩文化”和慢下来的重要性的文章读出来做成了视频,仅仅修改了标题和几个形容词,结果这个视频成了爆款。和人工智能相比,这个抄袭者读完了原文,选择了抄哪些段落,修改哪些单词,这种老式抄袭的技艺在自动化的过程中消失了。2023年,一个账号名为LindyMan(编注:这个名字显然取自lindy effect,林迪效应指的是经久不衰的事物——如技术或创意——已经存在的时间越久,在未来也会越长寿)的推特用户做了类似的事情,这个账号专门发布关于传统价值观和永久智慧的推文,内容全部来自《大西洋月刊》的旧文和被遗忘的博客文章。抄袭行为曝光后,他把责任推给了一个不存在的研究助理,然后继续发帖,至今仍然活跃在X上,并且很可能从马斯克制定的分成机制中获利颇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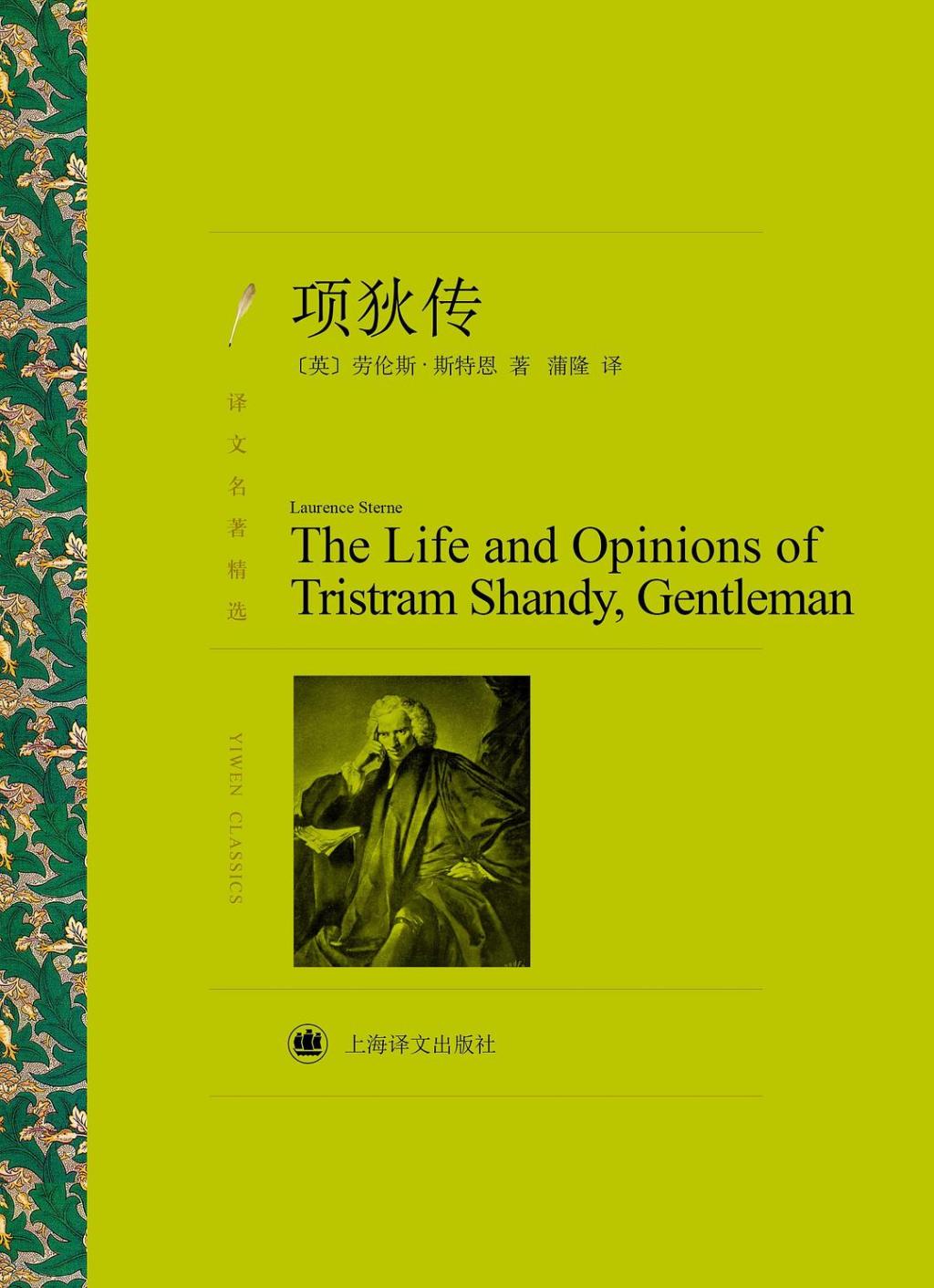
在巴特曼看来,偷窃内容这一行为源远流长。例如劳伦斯·斯特恩在创作《项狄传》时盗用了罗伯特·伯顿的《忧郁的解剖》,而后者本身就是一部拼凑和组装的作品,以过于较真的现代眼光来看也是抄袭之作;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则从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文学传记》中剽窃了整整一节。和今天只是复制粘贴的抄袭者相比,他们对偷来的东西进行了改进,使之成为了更好的作品,换言之,在盗窃时至少展现了一些品位。他们或许会声称自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继续建造,与纯粹的抄袭相比,他们有意识地选择如何使用他人的想法。
文章接着指出,过去我们认为,某些想法或是包装某些想法的方式属于某人。如果我想用你的想法,就通过引用并注明出处来表达对归属权的认可。尽管这个系统并不完美(它更有利于那些锱铢必较的人,而不是大大咧咧但富有创造力的人),但它基本上运行如宜,激励着人们不断进行微小的创新。人工智能彻底打破了这一现状,当一个语言模型同时用大量来源不明的文档进行训练时,其产出的归属权就变得模糊不清。美国新闻网站CNET的AI记者被发现大量抄袭竞争对手甚至CNET自己人类作者,它对现有文章进行重新合成而不注明出处,Futurism网站称之为“自动抄袭机器”。当教授们评估AI的作品时,他们表示其抄袭程度显然达到了足以让人类记者被解雇的程度。
巴特曼表明,关键始终在于人们怎么使用人工智能,大多数人不会用AI来提升自己的想法或探索新的联系,而是用机器来逃避所有思考。机器负责生成文本,人类只负责输入提示,接收内容,发布内容,然后收集点赞、订阅和分成。因为归根到底,发帖就是为了售卖。当人人都在抄袭,人人都在兜售时,这些词语就失去了原有的道德分量。就和指责人们出卖自我一样,说一个人说抄袭者或许符合事实,但实际上已经毫无意义。他进一步指出,很快大多数在线内容将由人工智能生成。谷歌的追踪显示,搜索结果中的人工智能内容在短短一年内就从10%跃升至近20%。到2027年,在网上寻找“原创”的人类思想就将像在沙滩上寻找一粒特定的沙子一样困难。
巴特曼进一步指出,人工智能生成的文本对于信息环境的污染与化学物质对物理环境的污染如出一辙。那些关心原创性、真正阅读思考写作的人根本无法与这些黑暗的撒旦式内容工厂相抗衡。而当抄袭机器吞噬了所有的原创内容,主要依靠彼此的输出进行训练时,就会发生研究人员所说的“模型崩溃”,生成越来越千篇一律、平淡无味的无意义内容。讽刺的是,那些靠抄袭机器发财致富的人却非常注重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OpenAI像保护国家机密一样保护着它的训练数据和模型权重,任何尝试对其进行解码的人都会被起诉。
文章最后写到,我们正在驶向一个美丽新世界,那里一切都是抄袭的,没有任何东西有归属,所有人都在租用流媒体空间,但没有人购买真正的内容。机器将生成内容,算法将分发内容,指标将决定成败。人类最好的结果是只负责输入提示和发帖,最坏的情况则是沦为人工智能深度伪造的样板。
巴特曼认为,或许我们已经没有出路,至少出路不可能是更好的抄袭检测或更严格的学术诚信政策,这些无异于螳臂当车。如果还有一丝希望的话,那或许存在于人们重新记起我们最初是为什么要推理和争辩,不是为了点赞、订阅或是教职,只是因为把事情弄清楚的感觉很好,赤手空拳创造出新东西是我们人类仅剩的少数几种真正乐趣之一。

《黑镜》第七季第一集剧照
如果说巴特曼笔下AI内容抹平一切的未来仍有些抽象,那么聚焦技术内容的发布平台HackerNoon日前发布的“人工智能的垃圾化是否已在进行中?(Is AI's Enshittification Already Underway?)”一文中,作者维克·波格丹诺夫(Vik Bogdanov)提供了更具体的警示。
“Enshittification” 是澳大利亚麦考瑞词典(Macquarie Dictionary )去年选出的年度词语,其定义是“平台逐利而出现服务质量的下降、服务和产品的逐渐恶化,尤其是在线平台的恶化。早期的互联网带来了解放,但快进到今天,互联网已经充斥着伪装成内容的广告、弹窗横幅广告、付费墙、垃圾索引和点击诱饵——全都是为了吸引关注和金钱。这种转变并非在一夜之间发生的,而是平台优先考虑利润而非用户体验的渐进结果。
当人工智能也像互联网一样开始大规模地把利润放在用户之前,会发生什么呢?波格丹诺夫认为,这种转变已然在发生。
首先,广告会被无声无息地插入人工智能生成的回复当中,这些广告甚至不会被标注出来,而人工智能的付费“推荐”服务不是一个未来概念,而是正在酝酿中的商业模式;其次是付费墙和用户甄别,今天免费的内容可能明天就需要付费,或者只有付费才能获得高质量的内容,一些公司可能不再面向人类用户,而只为其他机器人提供有偿数据服务;人工智能还可能对用户进行行为操控,不仅销售商品,还会塑造观点;动态定价可能会发挥作用,人工智能了解你的偏好、收入和消费习惯,它可能会根据你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收取费用……
人工智能的垃圾化可以避免吗?该文提到,一些人认为订阅模式能够阻止这一趋势,但另一些人认为这充其量只是一个垃圾化悄然发生前的缓冲地带。还有一些人认为,开源和监管框架才是真正的防御手段。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