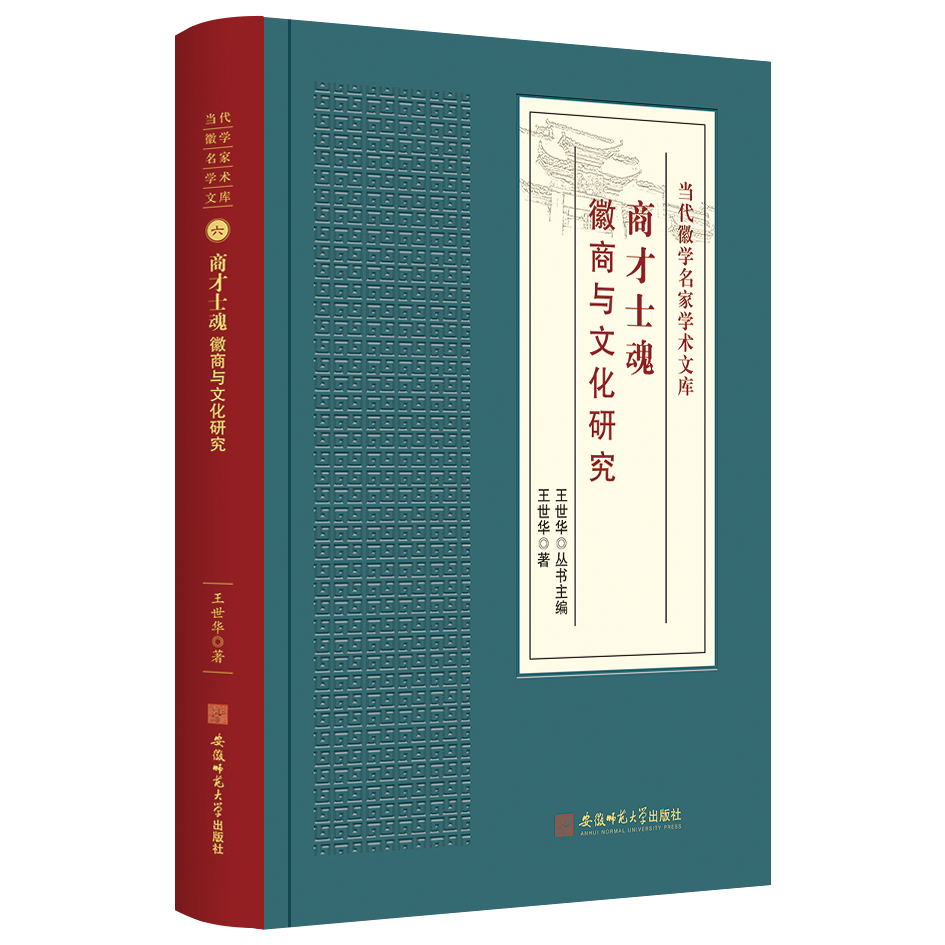
《商才士魂:徽商与文化研究》,王世华著,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6月版
说来真惭愧,我竟然是被“逼”着走上徽学研究之路的。
20世纪80年代初,我由党史教研室转入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决定跟随先师张海鹏研习明史。工农兵学员出身的我,自然学无根柢,因此暗下决心,咬定青山,从读基本史料做起,并逐渐培养起对明史的兴趣。谁知不久,先师决定开展徽商研究,并组织王廷元、唐力行和我成立了明清史研究室。先师极其重视收集资料,于是我们利用寒暑假下徽州、上北京、到合肥、赴上海查找资料。在当时非常艰苦的条件下,我们克服了种种困难,收集了一批资料,并于1985年出版了《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在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按说,此时研究条件已经不错了,只要努力,完全可以出成果的,可是我却“身在曹营心在汉”。那时我正钟情于明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沉溺在明代监察制度的研究里,对徽商研究毫无兴趣。先师虽也常常布置研究任务给我,但我常常敷衍塞责,往往引起先师的不快。只有在先师逼急了,才放下我的爱好,很不情愿地搞起徽商研究,《论徽商的抗倭斗争》《“左儒右贾”辨——明清徽州社会风尚的考察》等文章就是这样逼出来的。交差后我又搞起我的明代政治制度史研究来。
我资质中下,没有“双枪老太婆”左右开弓的本事,更没有“目送千里雁,手弹七弦琴”的能耐,两条战线作战,肯定捉襟见肘、狼狈不堪,自己累得要死,还事倍功半。成果出不来,先师也时时紧逼,我陷入痛苦的煎熬中。就这样,五六年过去了。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想,这种状态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既然我生活在这个集体,就应服从集体的需要,于是我忍痛割爱,断然放弃明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投入徽商研究中来。徘徊让我耽误了很多时间,加上当时家庭重担、教学负担也压得我够呛,即使被“逼”转向,也少有余力,故也没贡献出什么像样的成果。
紧接着,从1995年开始,我担任了学校的一些行政职务。由于工作任务重,大多数晚上九点后才能到家,只有这时候才能坐下来看书写作,在此期间我的所有文章都是这样写成的。其间的酸甜苦辣,真是难以为人所道。
2012年,我终于退休,这下才算彻底“解放”了。“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清静下来,看看自己“草盛豆苗稀”的学术园地,猛然感到,十多年已积下多少应读未读的书啊,无论如何是无法弥补,只能仰天长太息了。原计划是退下来好好读点书,不想一个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以及纷至沓来的各种事情又占据了我的大部分时间,徒叹奈何!
今天我只能怀着惴惴之心,将此不像样的书奉献给大家。书中的文章也是这些年来我思考的结果,我之所以将它命名为《商才士魂:徽商与文化研究》,就是越来越感觉到,徽商之所以能崛起,文化确实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观念的解放促使徽州人走出深山,踏上商途;文化又使徽商能够汲取历史上的商业伦理、经营之道,创建了商业制度,使他们成为历史上最成功的商帮;对文化的热爱使他们成为“贾而好儒”的商帮,彰显了徽商的最大特色,同时又使他们自愿倾以最大热情支持各种文化事业的发展,培育了大批文化精英,文化精英又创造了大量精英文化。徽商以空前的热情举办公益事业,赈灾济贫、修桥铺路等,又何尝不是受到文化的熏陶?徽商的一切都可以从文化上找到根源,甚至连徽商的衰落,也能归结到传统文化束缚的影响。文化可谓徽商之魂。这种文化即传统儒家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说是士文化。“画眉深浅入时无?”只有留待众人评判了。
书中的文章毕竟是在三四十年期间写就的,文中的观点肯定有的显得陈旧,为了尊重史实,一概保持原貌,不做改动。这一期间又是学界变化很大的时期,改革开放早期,由于还没有与国际接轨,学术规范上存在一些问题。本次结集时,早期的一些文章,除了在注释上进一步规范外,研究史回顾就无法弥补了,还望读者能够谅解。
特别要声明的是,本丛书命名“当代徽学名家学术文库”,我无论如何难当“名家”之衔的,本不应滥竽充数,后在一些师友的劝说下,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把自己的成果亮出来,也好争取同仁们的指教。古人云:“良工不示人以朴。”我虽不是“良工”,但要想获得他人的批评和帮助,何妨“示人以朴”?于是自贾余勇,不揣谫陋,编成此集,只能算是续貂吧。
本文为《商才士魂:徽商与文化研究》自序,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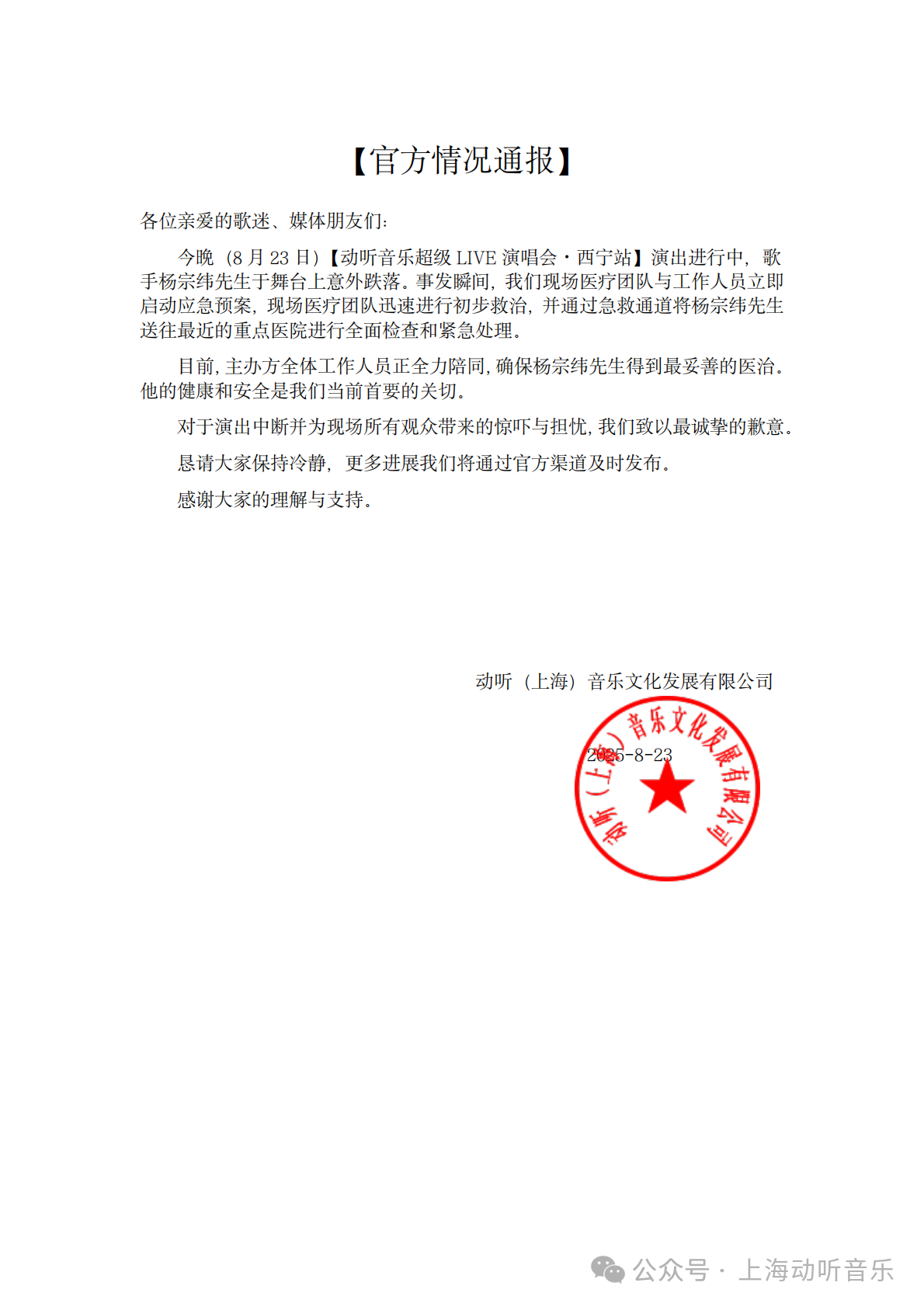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