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税不是什么新意思,但它为普罗大众所关注并津津乐道,还是要拜特朗普2.0所赐。
据《牛津词典》,关税指“对进入或离开一个国家的货物征收的税款”。作为贸易的一部分,它已经存在了数千年,塑造过帝国的辉煌,也酝酿过经济体的衰落。
古代和中世纪的关税
关税的历史与有组织的贸易一样长久。青铜时代(公元前3000至2000千年),古亚述贸易殖民地卡内什(位于安纳托利亚)的商人记录显示,当地统治者对从事金属和纺织品贸易的商队征收税款。尽管征收这些税款,亚述商人仍然从中获利,并将关税视为经营成本。
古代国家利用此类关税来增加国库收入并规范贸易。例如,在古希腊,雅典在其比雷埃夫斯港对谷物等重要进口商品征收2%的关税,以满足城邦的需要。罗马帝国也同样制定了关税制度,罗马各行省的内部贸易税率约为1-5%,而从亚洲或其他外部地区进口的奢侈品则面临更高的税率(通常为12-25%)。这也是为什么普通罗马人买不起丝绸和香料。
在中世纪时期,关税在欧洲各地逐渐系统化。12至15世纪,随着商业的复兴,封建领主和君主在城门和贸易路线上征收通行费。在中世纪的英格兰,羊毛是经济的基础,出口要缴纳高额的关税——通常相当于每袋几先令——以保护这一支柱产业。
类似的关税也适用于皮革、锡和奶酪等其他商品。这些关税带来了收入并保护了当地生产商,但同时也刺激了走私和逃税行为,例如,谎报应税货物的成分。这种做法直到今天还在继续。
中世纪的关税实践,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关税制度奠定了基础,亦即——关税通过调节贸易来服务国家利益,本质上是一种政策工具。
重商主义与早期现代关税
16世纪至18世纪,欧洲列强奉行重商主义。在这种思维模式下,一个国家成功与否与其国库中黄金的数量直接相关——而无论其公民的生活水平如何。因此,当时的领导人自然会努力最大化出口(这会将黄金带入国内)同时最小化进口(这会将黄金带出国内)。
高关税是欧洲重商主义政策的标志。从都铎王朝的英国到波旁王朝的法国,统治者都试图通过征收高额进口关税甚至直接禁止进口来保护国内产业,并最大限度地减少进口,尤其是制成品的进口。例如,在都铎王朝君主以及后来罗伯特·沃波尔等斯图亚特王朝顾问的主导下,英国对外国制成品征收高额关税、补贴出口,并禁止可能与宗主国竞争的殖民产业。
直至1720年,英国对进口制成品征收的平均关税高达45-55%。而在关税的防护墙后,英国培育并发展起自己的纺织和金属工业。类似的保护主义措施在让-巴蒂斯特·柯尔伯特执政的法国也曾出现,他通过征收高额关税来扶持法国工业和海军。西班牙和其他殖民列强也禁止其殖民地自由贸易或发展竞争性制造业。在重商主义者看来,关税是压制对手、充实国库的利器,哪怕这意味着本国公民需要承受更高的物价。
与此同时,一些思想家开始对重商主义观念提出质疑。18世纪中叶,法国的重农学派主张粮食自由贸易,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则对重商主义关税进行了尖锐批评。斯密认为,保持低关税和减少贸易限制将惠及所有国家,“关税和其他税收通常只会增加消费者的商品成本,并抑制工业发展,而‘自由出口和自由进口’则能让每个国家专注于其最擅长的生产领域,从而实现繁荣。”
这是经济学理论的一次革命性转变。此前从未有人提出自由贸易而非保护主义才是实现国家财富的途径。1817年,大卫·李嘉图通过比较优势理论强化了这一观点,他指出,即使是一个在各方面都很强的国家,也都能通过专注于其最高效的产业并进口他国产品而获益。
这样,古典经济学家就为降低关税提供了理论基础。不过,和其他新兴理论一样,这些自由贸易理念进入主流需要时间,转化为政策则需要更长时间。
关税、工业化和18至19世纪的改革
18世纪末和19世纪,秉承斯密和李嘉图的古典经济思想,各国就关税政策展开了激烈争论和变革,尽管具体政策的差异很大。在美国,关税最初被视为联邦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第一届美国国会于1789年颁布《关税法案》,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增加税收。
19世纪的前几十年,为了安抚依赖出口棉花和进口工业品的南方农业州,美国关税税率一直较低。但保护新兴工业的压力日益增大,1828年,北方制造商推动通过了一项大幅提高关税的法案。
这项法案毫无意外地被南方斥为“可憎关税法”,几乎引发了一场宪法危机——南卡罗来纳州威胁说,要么废除法案,要么它退出联邦。1833年,联邦政府最终妥协,降低了关税。对美国决策者来说,这是关于关税的重要一课——关税激化了受保护的工业利益与原材料出口商之间的矛盾,导致地区政治的紧张局势。
与此同时,在英国,关税政策却走向了不同的方向。作为世界上首个工业化国家,它已经确立在制造业的优势地位,倡导自由贸易的呼声逐渐汇成主流。不过,在19世纪20年代中期以前,英国政府始终坚持重商主义(工业进口关税平均约为50%)直到1846年,英国议会才废除了臭名昭著的《谷物法》,结束对进口谷物的高额关税。
《谷物法》自1815年起实施,通过禁止进口廉价谷物,将英国谷物价格(及地主利润)维持在高位。1845年,爱尔兰爆发大饥荒,民众奔走呼吁廉价食品,成为废除这一法律的契机。而该法的废除意味着从此谷物可以自由贸易,这也是英国正式接受自由贸易原则的开始。此后数年,许多其他商品的关税也相继降低或取消。
不过,英国单方面推行自由贸易的举措,并未立即引发其他国家的效仿。1841年,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就曾提出,像德美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应该效仿的是英国(过去)的做法(即利用关税来发展工业),而不是英国(现在)的说法(即自由贸易)。李斯特指责英国藉着高关税的梯子爬上工业霸主的宝座,随即就“踢开了梯子”。
美国为保护其蓬勃发展的钢铁和制造业,在内战后采用了极高的关税。1860年代至19世纪末,美国对应税商品的平均进口关税高达40%-50%,成为贸易保护主义在那一时期的堡垒。
美国早期领导人,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有一套“新生产业论”,认为新兴产业在成熟前需要临时关税保护。根据这套理论,美国拒绝了李嘉图的自由贸易建议,得以快速实现工业化。
在欧洲,俾斯麦于1871年统一德国,随后就放弃了先前的自由贸易实验,1879年起对铁矿石和谷物征收关税,以保护德国的工业和农业。
这样一来,在19世纪末,一个清晰的贸易图景就呈现出来了:率先工业化的英国提倡自由贸易,而美、德等新兴大国则维持高关税,以期在经济上迎头赶上。
上述政策差异带来了一些可量化的结果:
这产生了可量化的影响。
从1870年到1913年,英国的工业增长约每年2%,落后于采取保护主义政策的美国和德国(每年4-5%)。一些人认为,关税是后者增长更快的关键因素——尽管其他因素也起到了作用,包括自然资源禀赋和国内市场规模。
在西方以外的地区,欧洲列强则寻求并强加对自身有利的片面关税优惠,许多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被迫开放市场,施行自由贸易或低税率、统一税率的关税制度。通过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它们迫使中国和日本接受进口关税上限(通常约为5%),侵夺了这些国家关税自主权。例如,鸦片战争后,中英《南京条约》将中国关税固定在名义上的5%,导致中国市场被大量外国商品淹没。
可以说,19世纪的“全球自由贸易”是由帝国主义强加的。在欧洲,英国和法国宣扬自由贸易,一旦到了其殖民地或势力范围,则往往强制实施自由贸易或低关税,以便为自家商品打开当地的市场。反过来,如果殖民地或势力范围想要通过保护性关税来实现工业化,它们是不会同意的。
20世纪初:关税、战争与萧条
20世纪初,全球关税水平总体上处于较高水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多数大国都对关键产业实施了保护措施。20世纪20年代初,美国对制造业的平均关税保持在40%左右,拉丁美洲及其他地区的新兴国家也往往依赖关税作为财政收入和产业发展的主要来源。
一战后,欧洲有过短暂的削减关税的尝试(1920年代,一些国家降低了关税壁垒),但很快就被经济动荡淹没了。
20世纪30年代,随着大萧条的到来,保护主义大行其道,各国竞相大幅提高关税,国际贸易也由此坠入了深渊。其中最为臭名昭著的是美国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为了庇护经济萧条下的美国农民和工厂,该法案一举将对超过1万种商品的进口关税提到史无前例的水平(可征税商品的平均关税高达60%)。作为回应,加拿大、英国等国纷纷对美采取报复性措施,或提高关税,或将贸易转向其他国家和地区——例如,曾是美国最大贸易伙伴的加拿大,便将贸易转向了英国帝国。
如此恶性循环,世界贸易严重萎缩。尽管现代经济史学家认为,大萧条的主要原因在于货币和金融崩溃,但以邻为壑的关税战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全球经济衰退。
二战后:GATT和WTO框架下的自由贸易
二战的终结,标志着全球贸易政策的重大转变。1947年,以美国和英国为首的23个国家签署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其核心原则是通过一系列谈判逐步降低关税,从而避免重蹈20世纪30年代贸易战升级的覆辙。
在这一框架下,全球关税水平降至历史最低水平——1947年,GATT/WTO成员的平均关税约为22%,到1994年,这个数字已降至5%以下。历史由此进入贸易扩张的时代。
这种转变源于战后形成的经济共识,即自由贸易促进增长。这显然是凯恩斯主义和古典经济学理论催化的结果,也因为保护主义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失败而得到了强化。与关税削减相辅相成的,是区域贸易集团的形成。在欧洲,欧洲经济共同体(后来的欧盟)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建立了关税同盟,在取消成员国之间内部关税的同时,对外实行统一关税。1992年,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致力于取消北美地区的大部分关税。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同样也出现了许多旨在降低关税、促进贸易的区域协定。
当然也有例外。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根据“新兴产业理论”,许多发展中国家采取了进口替代战略,通过维持高关税来扶持国内产业;还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四小龙”通过选择性保护和补贴措施来培养有竞争力的产业——这与早期重商主义策略相呼应;不过,随着产业的成熟,这些国家和地区也逐渐开放了市场。
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建议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开始降低关税,并加入WTO。
21世纪初:贸易摩擦与趋势
21世纪初,平均关税税率处于历史低位,但关税并未消失,贸易争端也未消失。全球供应链和自由贸易协定蓬勃发展,但一些国家出于经济或战略原因,不时将关税作为政策工具。
2010年代末,关税战卷土重来。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内,以不公平贸易行为和保护国内产业的需要为由,提高了对数千亿美元进口商品的关税,目标直指钢铁、铝,尤其是中国商品。中国和美国其他贸易伙伴则对美采取了报复性关税。截至2019年,美国已对超过36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新关税,中国则对11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了报复性关税。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关税组合拳更是花样百出,包括新关税、关税威胁、临时豁免以及针对传统对手(如中国)和传统盟友(如加拿大、墨西哥和欧盟)的更多关税。WTO规定其成员不得随意提高关税,但对美国这样的大国的约束力十分有限,后者往往以国家安全或其他例外条款为由使用关税工具。
与此同时,各国也出现了反对自由贸易的声浪。批评者认为,快速的贸易自由化既会损害高收入国家制造业工人的利益,又可能被威权国家用作施压的工具。他们呼吁通过实施战略性关税来保护关键产业或解决贸易失衡问题。
眼下这一轮关税争端到底会带来怎样的影响?目前尚不明朗。但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正如他们在1930年代评估的那样,总体而言,高关税会推高物价并引发报复性措施,从而损害社会经济的整体福利。
结论
从历史的长时段看,关税具有两面性:对于年轻的美国和德国而言,它有助于新兴产业的发展,同时为财政带来收入;然而,在饥荒时期的爱尔兰,它却导致了大规模饥荒;到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关税引发大国间的贸易战,使得本来就严峻的经济形势雪上加霜。
关税的历史,并不像乐观的人们预计的那样,以自由贸易对保护主义的普遍胜利而告终。作为一种有韧性的政策工具,“关税”在21世纪初的贸易冲突中重新成为焦点,一些国家开始调整其相关政策,以解决就业、安全或公平方面的担忧。
漫长的历史表明,尽管征收关税的理由会变化——从为帝国提供资金到保护新兴产业,再到报复不公平行为——但保护国内利益的愿望与开放市场利益之间的根本矛盾仍将持续存在。对决策者而言,真正的挑战不在于关税的有无,而是如何在其两面性之间取得平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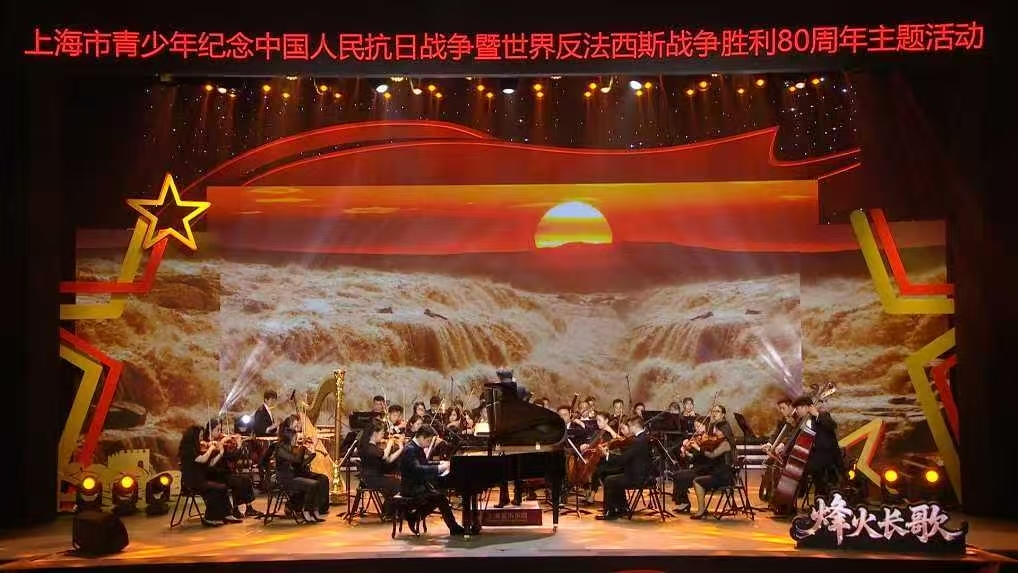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