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东亚女儿的自我怀疑里,藏着母亲的话语。自责的根,原是太想成为“值得被爱”的女儿。母亲也是在父权制中跌跌撞撞从某人的女儿成为一个女孩的妈妈。无论是母亲还是女儿,
她们都在面对同一个迷宫。母女关系的复杂之处在于,双方逐渐以各自的方式预判对方的反应,从而导致关系中负面因素被不断放大。本文摘自日本临床心理医生斋藤环的《母女关系的精神分析:被支配的女儿们》,澎湃新闻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授权发布。
母亲是“真凶”吗?
我开始写这本书后不久,在某次讲座上,一名茧居女性提问,她在为母女不和而苦恼,我写的书里有没有这方面的内容。
在不和外界发生接触、长期居家的茧居者心里,往往积蓄着和家人之间的矛盾压力。大多数情况是家人不欢迎他们茧居,于是形成与家人之间的对立。可以说,茧居者基本上都会因为家庭关系而苦恼,不过能提出这类问题的几乎都是女性,尽管茧居者中绝大多数是男性,是家庭中的儿子。所以这种现象更显奇妙。
在本小节里,我想从临床经验出发,探讨母女关系的复杂性。
临床医生谈到母女关系时,通常会把母亲当作“起因”和“犯人”。虽然情况现在已经有所改善,但过去曾有一段时间,各种精神障碍病状都被归因于母亲育儿方式的理论颇为流行。比如“母源病”、“坏母亲理论”、“三岁定终身理论”(幼儿期母亲若是不专注于育儿,将负面影响孩子的一生),等等。甚至有一个时期,连已经确认为大脑疾患的自闭症都被归咎于母亲的养育方式。
我本人不关心,也不太信任以上假设。家庭关系是一种拓扑关系,其成员不一定非得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家人,这是我的基本观点。如果只靠责备父母就能解决问题,那临床工作会轻松很多。但轻松并不能带来收获。
即使母亲的育儿方式即病因的说法是正确的,本书也不做详细探讨。不过,通过各种临床病理能够清楚地看到潜藏在母女关系中的问题结构,所以本书不可避免地要涉及病理。接下来,我会不时提及一些实例。在此提前说明,实例的一部分来自我的临床经验,一部分引自论文。为了保护隐私,会对细节问题做模糊化处理。
关于母女关系的复杂性,我常想起这个事例。这是一个长期咨询案例,一名母亲前来咨询女儿拒绝上学的事。她的存在感极其强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女儿已经成年,年过二十岁依旧处于母亲的支配之下,似乎理所当然地接受了母亲的控制。这种情况只要不引发问题,也可视为一种生活方式。不过,最初的问题从女儿拒绝去学校、居家不出开始,毕业后又转变为无法适度地与异性交往。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基本上是女儿对外貌的自卑感,以及在建立异性关系时的罪恶感。这几乎都源于母亲的强大影响。陪同女儿前来的母亲紧追不舍地问:“我该怎么办?”通常我很注意避免对就诊者和家长做出过分肯定的结论,不过这一次我忍不住脱口而出:“首先,您可以停止控制您女儿的生活,不妨试一下。”
听到这一指摘,这名母亲异常愤怒,仿佛受到了无端的诽谤中伤,她以要诉诸法庭的架势痛骂了我一番。我不是冲动之下才说此话,而是在长期接触这对母女之后逐渐形成了看法。我试着向她这样解释,但情绪激动的母亲完全听不进去。
最终,那天发生的事终结了我们的诊疗关系。至今我依然认为,这名母亲之所以激怒,是因为我的指摘击中了她的痛点。但我也做了反省,应该在措辞和发言时机上多做细致考量。
回想起来,这名母亲经常不预约就堂而皇之地前来就诊,已经过了规定的咨询时间依旧强行延时,炫耀亲属是公司高管,流露特权意识。这些都让我很难处理医患关系。她的强烈个性里似乎浓缩了“坏母亲”的典型特质,可能正是这些刺激了我,让我冲动之下起了反感。对此类母亲形象的过度抵触是我作为诊疗者的一个弱点。我与我母亲关系并不糟糕,这种情绪源于何处,我也说不清楚。
通过这个事例,我意识到母亲的支配力量可以多么强大。如果说这段经历促使我写了这本书,那我应该感谢这名母亲。
说到临床常见的母女关系引发的问题,我会首先想起进食障碍。出现进食障碍的人几乎都是女性。做家庭病理研究几乎都会涉及母女关系,不过,这种病理不仅仅适用于进食障碍,更可以应用到尚未达到病态程度的母女关系上。下面的事例堪称典型,引自一本介绍家庭健康疗法的书籍。
二十三岁的女性A经历求职之后,出现暴食、呕吐、无月经等症状,遂去精神科就诊。A 的母亲认为女儿中了某种邪,于是加入某个宗教团体,并强迫A也信教。最初A对母亲的话半信半疑,慢慢地她也开始相信邪灵确实存在,自愿和母亲一起去参加宗教集会。她被精神科医生问到这一点后,为母亲辩护道:“我这种状态让妈妈很不好过,妈妈为了让我好起来,甚至牺牲自己的工作定期参加信者集会。”另一方面,母亲则一口咬定:“这孩子柔弱不能自理,真的是废物小孩,永远在等着我去为她做什么。”
就这样,A和母亲之间保持着强有力的感情纽带,与此同时母亲无法理解女儿真正的欲求,她兀自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感情强加在女儿身上。A自幼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长大,自身也无法感知自己的感觉、情绪和渴求,无法以一个独立个体去表达自己的想法。从某个角度看,A的进食障碍可以视为她对母亲的抗议,只是A自己并未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一种抗议。她和母亲过分紧密的相互依存状态,以及母亲的支配性的权力让她恐惧,导致她自行关闭了反抗的思考回路。
B的例子在过度依赖的倾向上与A迥异。
二十岁的女性B,因显著减轻的体重和无月经去精神科就诊。她已是成年人,却对母亲保持着幼儿型的依赖关系,两人形影不离,没有任何隐瞒。母亲也积极地照看她,父亲则退后一步,持观望守护的态度。父母之间的对话基本上谈的都是女儿B,从来不提及彼此的不满。B和母亲形成了一种过度密切的关系,她从未和比她大六岁的姐姐一起玩耍过,也从未有真正的交友关系。
在我的印象中,比起进食障碍,B的问题类型更多见于茧居者。B和母亲的关系堪称一种典型的母女关系模式。
接下来的C,在进食障碍之上,还有边缘型人格障碍。
二十二岁的女性C和母亲是二人家庭。C和母亲紧密地互相依赖,同时又对这种状态焦躁不满。C总说:“我想和朋友出去旅行,妈妈就会很生气,说我丢下她一人,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妈妈怕寂寞,离不开我,我懂她,所以我没法出去旅行。”
同一件事从母亲的口中说出则是:“C是个娇气孩子,我拿她没办法。她怕寂寞,离不开我,所以我连旅行都去不了。”
出现这种情况,可以认为问题出在两人之间的过度依赖上。
《金色牢笼》——迎合母亲期待的女儿
当然,进食障碍的原因不仅限于母女关系,最近有研究认为背后还有生理学因素。不过本书的观点是进食障碍属于心理问题,而非大脑病变。众所周知,进食障碍与减肥、追求极致瘦等现代风潮密切相关,如果病因真的在大脑,那么进食障碍应该是不分时代和地域、更具普遍性的疾患。
从各种文献来看,进食障碍的家庭病理中包含了许多与母女关系相通的要素。
比如研究进食障碍的权威专家、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希尔德·布鲁赫(Hilde Bruch)在著书《金色牢笼:厌食症的心理成因与治疗》(The Golden Cage:The Enigma of Anorexia Nervosa)中提出以下观点:
从数据上看,进食障碍者的家庭中,所谓的衰败家庭并不多见,大多是中流阶层以上,父母对孩子充满关爱,表面上看不到显著的“病理”。往往在看似和平的家庭关系下,潜藏着强烈的紧张。母亲经常以自我为中心和孩子相处,背离孩子的需求;孩子常常感到自己被母亲过度控制。换句话说,一个家庭尽管在外人看来幸福美满,孩子却感到母亲的期望和束缚剥夺了自己的自由。《金色牢笼》的标题暗示了这些孩子身处优越家庭环境下却被禁锢的矛盾状态。
布鲁赫的书里有一个颇有意思的点,是由一名克服了进食障碍的前患者提出的,她认为,这个牢笼也许是由她自身打造而成的。孩子在和家人,尤其是和母亲的相处中,有时会逐渐形成一套固定的行为模式,在该模式下,孩子常常主动抑制自己的欲求,去迎合父母的期待,而这一切仅仅是为了让父母满意。
布鲁赫的书现在依然拥有读者,不过书中介绍的进食障碍的典型事例,现在似乎有所减少。重新阅读这本书,会发现其中描述的病理正以另一种普遍性的方式存在。布鲁赫指出,不仅是母亲在控制女儿,有时女儿一方即使内心充满纠葛,也甘愿被母亲控制。这一点十分契合现代的母女关系。如此看来,“金色牢笼”可谓无处不在。
布鲁赫还指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代名词的混乱”。
在进食障碍的家庭中,家庭成员各自以自我为中心,同时彼此关系紧密,有共享想法和情绪的倾向。问题在于,A方表现得好像完全理解了B方的想法,哪怕B方表示“你根本就不理解我”,A依然试图将自己的推测或想法强加给B,这就是“代名词的混乱”。这种倾向不仅限于进食障碍的家庭。在错综复杂的母女关系中,常常可以看到“我女儿就是这样”“我妈就是这种人”等自以为是的错误理解。
这里涉及的是“投射性认同”的心理机制,即将自己的情感误以为是对方的情感。例如,本来是自己因为对方感到愤怒,有时候却感觉到对方在对自己生气。投射性认同不仅带来这类错觉,还会将错觉再次强加给对方,从而影响对方的行为和情绪。例如,如果对方和你说话时,不断重复“你生气了”,虽然这是他强加给你的误解,但有时你真的会发火。
也许最初占领支配位置的人是母亲,但在这种不断互相强加误解和感情的过程中,母女关系也会逐渐变得异常纠结。也许有人会产生疑问:“这种关系不仅限于母女吧?母子、父女之间难道没有吗?”当然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只是在母女关系以外非常少见。
在情感层面上,同性之间更容易达成深层共鸣和认同。这里深深涉及身体性。不过虽说是同性关系,父子的组合通常要简单得多。一般来说,父子关系容易演变成简单的对立关系或权力争斗,父亲试图压制儿子,儿子要么反抗,要么勉强服从。母女之间的权力争斗中包含了通过共情和关怀而进行的支配控制,复杂多层,远超父子关系。母亲以“为你好”为堂皇名义,实际上试图将自己的欲求和理想强加给女儿。女儿则似乎预先感知到了母亲的欲望,表面上抵抗,终究难以违背母亲的支配。这种关系构架,有时是双方有意而为之,有时是无意识中构成的。通过深层的理解和共鸣进而相互依赖、相互束缚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只存在于母女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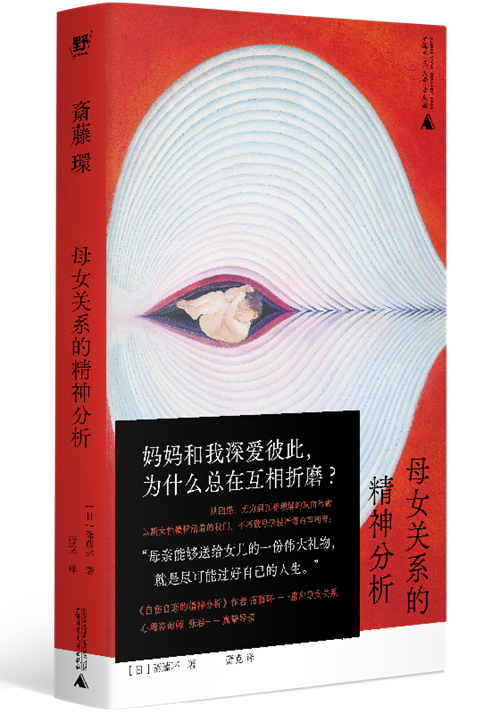
《母女关系的精神分析:被支配的女儿们》,[日]斋藤环著,蕾克译,野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7月。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