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聊斋志异》的改编势头不减,流行歌、动画片不断翻新。光是聂小倩故事,去年底至今就有老片新片在大银幕搬演三次,最新的《聊斋:兰若寺》甚至将其背景设定为民国。聊斋人物如此深入人心,将来或许会像哪吒一样成为文化输出的品牌。
早在六十多年前,张爱玲就想在美国传播“聊斋”故事。1959年6月3日,她在致好友邝文美的信中透露,自己曾向出版经纪人提出“聊斋改编TV”的构想,却遭到对方否决:“她说一切fantasy〔幻想作品〕都没销路,(science fiction〔科幻片〕已不是fantasy)但鼓励我想个方法在TV西部剧中灌入东方色素,如最近有个西部剧中夹进一个日本武士切腹。”
这一回应折射出当时西方对东方文化的表面化想象,他们需要的并非深层文化叙事,而是猎奇式的符号点缀。张爱玲后期英文写作屡屡遇冷,也意识到那时美国市场对中国故事的狭隘期待:要么是赛珍珠笔下的农民,要么是开洗衣店的华人。张爱玲不愿妥协去重复这些刻板叙事。
张爱玲是坚持自我风格的作家,作品大多基于真人真事,喜欢写有亲身体悟的细节。她从小爱读《聊斋》,晚年对狐鬼狂想曲兴趣渐淡,更喜从中窥见人情世理。她坦言连《夜雨秋灯录》《阅微草堂笔记》这类聊斋仿作都反复阅读,兴趣点总落在那些反映社会风气、真实感强的故事里。
回溯张爱玲在美国的经历,可知她想改编“聊斋”电视剧不是一时兴起。1955年刚抵纽约,她就对电视剧本创作产生兴趣;1957年眼见自己的作品《秧歌》被改编为拖沓的电视剧,很可能更坚定了她要亲手把握叙事的决心。至1959年正式提出构想,实为多年酝酿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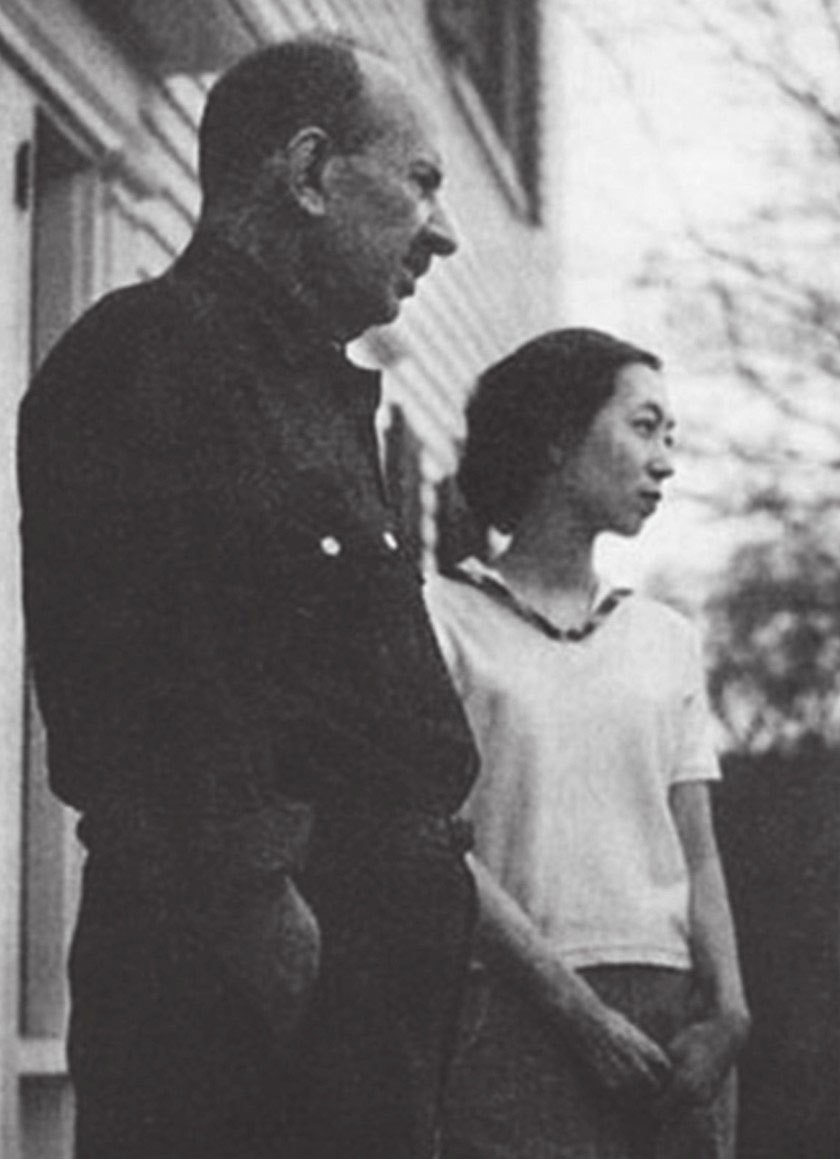
张爱玲与赖雅,1957年在美国
她对“聊斋”题材的钟情,可在1956年7月找到端倪。张爱玲当时已与美国作家赖雅(Ferdinand Reyher)定下终身,他们兴奋地谈论下一步写作计划,张爱玲提出两个英文题目:Bridge of Filial Piety,The Corpse Driver——这是传记作家司马新披露的,可能得自赖雅日记。司马新将它们译成《孝桥》《僵尸车夫》,认为取材于中国古代文学。
张爱玲文学遗产执行人宋以朗认为,Bridge of Filial Piety可能是“野史里清朝乾隆年间孝子王安为母建桥过河去跟和尚通奸的故事”,可译作《孝子桥》。The Corpse Driver则显得诡异,译成“僵尸车夫”使他联想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香港僵尸电影,他认为应改译《赶尸人》,指湘西“赶尸”传说,宋先生好奇道:“写法会不会像她喜欢的《聊斋》那样呢?”
确实是《赶尸人》更合理。香港友联公司于1956年3月出版发行过一本配有大量剧照的《湘西赶尸记》(英译名:The Case of the Walking Corpses)电影小说,同年6月张爱玲也在友联出过书,不知她会不会关注到此片?她当时虽在美国,但兼任香港“电懋”公司编剧,需要广泛搜集素材、留心影坛动态,好友邝文美也常寄赠香港报刊予其灵感。
而关于《孝子桥》,有个更确切的出处,也是在张爱玲阅读经验范围内的:清人韩邦庆著《太仙漫稿》小说集,《和尚桥记》一篇便是记叙这故事。
韩邦庆还撰有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对张爱玲影响极大。她赴美前还写信给胡适,发愿今后要英译《海上花》。她确实做到了,并把书中的沪语对白译成国语,大力在中西方推广这部小说。
张爱玲从小阅读的《海上花》是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新式标点本,由汪原放点校,胡适作序,刘半农评介。此版细节如标点样式及书末“几页字典”,她到晚年都记得很清楚。
亚东版也附录了《太仙漫稿》及相关《例言》,相信张爱玲不会错过。
韩邦庆曾在《申报》做广告,介绍《太仙漫稿》是“翻陈出新,戛戛独造,不肯使一笔蹈袭聊斋窠臼。”但时人仍认为它“笔意略近聊斋”。
《和尚桥记》不长,抄录给大家品鉴:
余友曹子甡孙,自郾赴新郑,道经长葛之孝子桥。或曰:是和尚桥也。盖乾隆末年,里有郭孝子,为和尚筑是桥云。
孝子幼丧父,母与某寺僧有私。孝子数几谏,母内自惭,然不能绝。孝子知母之不能绝僧也,阴禁不令通。僧故善媚,捧匜沃盥,惟母所欲;母亦昵事僧,无所不至。自绝僧后,母日思望,居不安,食不饱,寝以成疾。孝子惧,反招致僧以奉母,而母始瘳。
里故郑地,溱洧环村北,阻僧所居寺。僧祁寒夜来,不免厉揭;既就孝子家宿,胫股若冰雪。母谓僧为己故,益痛惜之,自以腹熨贴令暖,齿震有声,闻于孝子。孝子曰:“吾之忍而出此者,凡所以为母也。今若此,不为之所,且重得疾。”于是鸠工作桥。“孝子桥”以是名。他村相谩者,乃曰“和尚桥”。
既而母卒,孝子既哭而息,仰天叹曰:“吾之忍而出此者,凡所以为母也。母今死矣,吾将有以报吾父。”乃以讽经召僧。僧至,即灵前手刃之,首官请罪。官廉得情,拟流三年。呜呼!孝矣。
一说:僧即孝子父。父故无赖,以事遣戍,祝发而逃。孝子请返初服,不许,然犹时归家信宿,孝子阴卫护焉。桥当孔道,名“济众桥”,孝子藉其家财以筑之,非有他也。
张爱玲会选择这一题材并非偶然。《和尚桥记》中郭孝子与母亲复杂微妙的关系,与她自身经历形成某种映照。张爱玲在《小团圆》中写母亲蕊秋的多段恋情时笔触宽容,没有把她当作“风流罪人”去审判,甚至带有一份理解与悲悯,从西方小说、剧本里找到很多像她一样的母亲形象,去为她辩白:“她不过是要人喜欢她。”若张爱玲真的改写成《孝子桥》,想必不会简单批判伦理越界,而是透视人情深处的无奈与挣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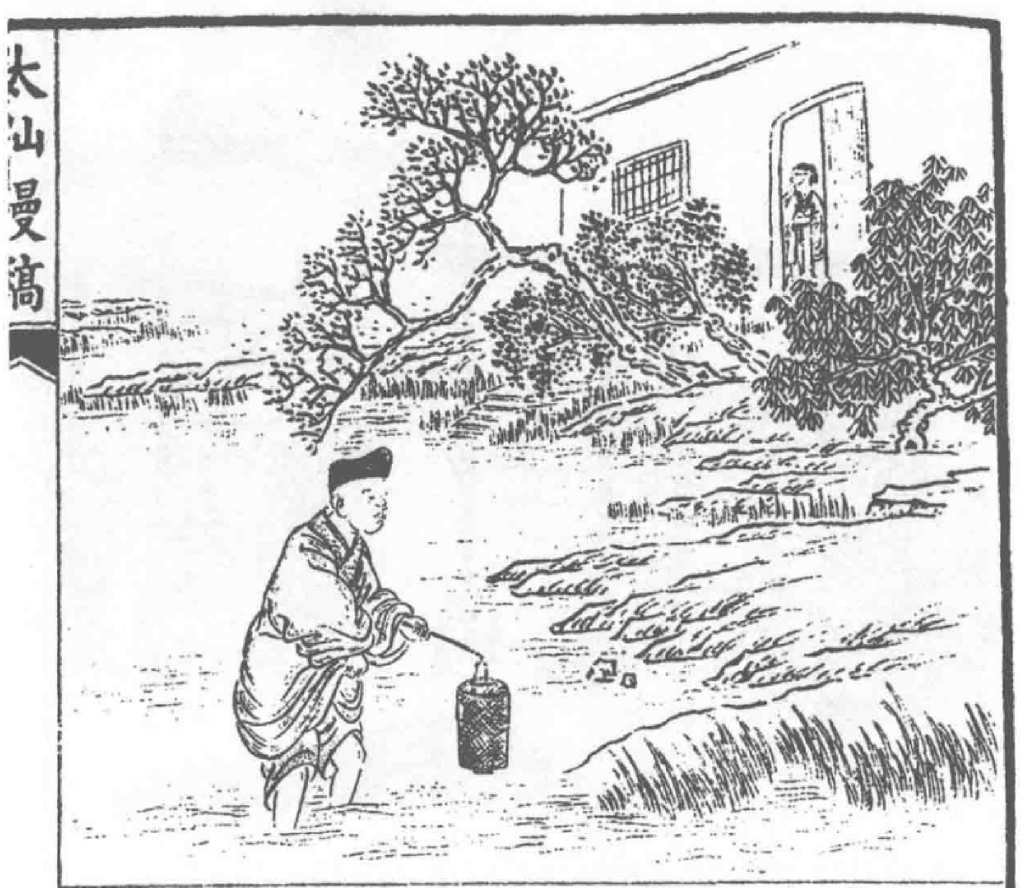
《和尚桥记》原版插图,初载1892年《海上奇书》第二期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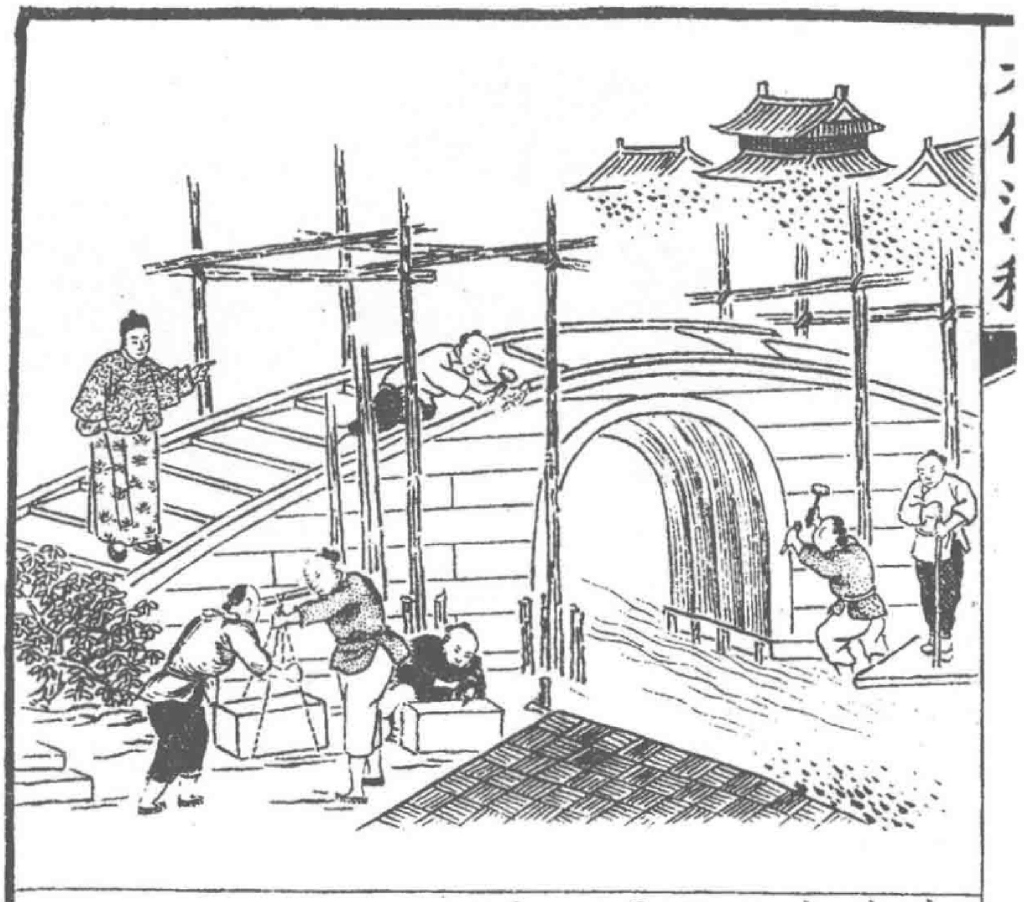
《和尚桥记》原版插图,初载1892年《海上奇书》第二期 (2)
韩邦庆笔下的这座桥,有三个名字,可代表不同主题:“孝子桥”突出身为人子的孝行,“和尚桥”是别村人眼中的奇闻艳事,“济众桥”则有替父赎罪的意味。
直到今天,河南省长葛市仍有一个以桥为名的“和尚桥镇”,据《长葛县志》记载,当地清潩河上昔有石桥一座,始建于明嘉靖年间,因和尚募化,得名“和尚桥”,万历年间曾改名“济众桥”。对于韩邦庆所写故事,当地文史研究者不太欣赏,认为是道听途说。还有人认为,全国的“和尚桥”不止一座,很难考究这“附会的传说”起自何地何时,又说明代小说已有这故事,但未列出证据。(见路志纯主编《长葛史话》)
其实,韩邦庆并非要坐实这个悖德故事,他在末段也记下了完全不同的版本:孝子父亲犯了事遭流放,削发为僧逃回来,劝他还俗也不肯,时常在家留宿两三日,孝子暗中掩护。孝子出资建造“济众桥”,因处关口要道,受惠的是大众,不只方便他父亲。杀僧情节自然是不存在了。
《和尚桥记》的动人之处在于,正文写实展现了郭孝子的内心挣扎变化,从多次劝谏到暗中阻止,母病儿忧,只好主动招僧来。他心疼母亲,她怜惜僧人,三人关系由一座桥联结,母亡不啻桥断,最终发生悲剧。
正如鲁迅评《聊斋》“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韩邦庆也自谓“于寻常情理中求其奇异”,张爱玲则始终践行着自己所说的“在传奇中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她想要的“聊斋”相关改编,注定不是离奇鬼话,而是逾越常轨的人间悲欢。虽然张爱玲未能将“聊斋”搬上西方荧幕,但她的尝试提示我们:真正的文化对话,从来不是投喂异域想象,而是讲述那些跨越时空地域的人性共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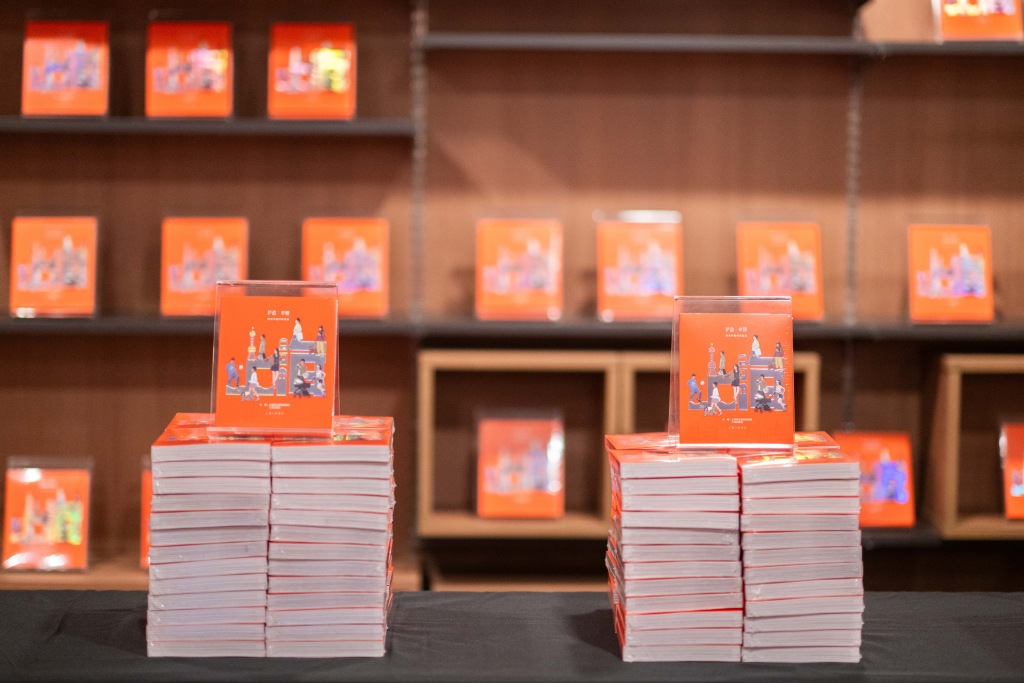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