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黄小荣
访谈人:黄毓婕
访谈时间:2022年3月7日、3月14日、3月29日、4月15日
访谈地点:线上访谈
访谈整理:黄毓婕
亲历者简介:黄小荣,男,1971年出生于福建省浦城县万安乡。1987年初中毕业后入读福建省建阳师范学校;1990年从建阳师范毕业后,被分配回原县籍地浦城县,成为九牧乡蒋坑小学的住校教师;先后任教于八所乡村小学,荣获市级、县级、乡级“先进教师”等荣誉称号;2010年,被调任至浦城县万安乡中心小学,先后兼任中心小学教导副主任、总务主任,在学区范围内推广电子学籍,负责农村小学、幼儿园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
一、教育让我摆脱农民的身份
我们家三代只出了我一位老师。我1971年出生在福建省浦城县万安乡大游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爸妈都是贫农,一家五口靠种田为生。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国家规定每户需要缴纳的稻谷任务数,每百斤可以兑现17元,余下的粮食能以每百斤19元6角的议价卖给国家粮站,比任务数价格略高。我爸是个勤劳的农民,为了多赚些钱,从那些决定外出打工的亲戚朋友那儿借一块稻田来种,连续种了两三年三四十亩的双季稻,最多的一年卖了一万斤,赚了1000多元。结果没想到1984年、1985年全国大丰收,国家粮站的议价也便宜了许多,每百斤只能卖到14元,那之后的几年,全国的粮食价格一直不高。我爸用存下的这些钱盖了新房,这栋房子一直住到现在。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家算是条件不错了。
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们村出过几个大学生。有一家人是村里的红人,妈妈是隔壁村小学的一个民办教师,有三个儿子,大儿子比我高几届,我读二年级的时候,他已经五年级了。这人从小学开始就特优秀,我记得每年学校办“六一”表彰会,村干部都会参加,按流程是先发县级表彰,再发乡和学校的表彰,领导在台上叫到“郭明”获奖,那人(上去领奖)刚拿着奖状和奖品下来,走到半路的时候,台上又叫:下一个“郭明”,他又跑上去领了,我们坐在台下一片哗然,这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后来他初中就被浦城一中录取了,最后考上南开大学,还读了研究生。大家都说他之所以那么优秀,是因为是老师的儿子。他还有两个弟弟,较大的那个叫郭辉,是我的同学,我们俩从小学开始就在一个班级,那时候经常是要么他考第一我考第二,要么我考第一他第二,两个人就这么比赛到中考。
我爸虽然没上过几天学,但很重视我们兄妹三人的学习,一天到晚要求我们要好好念书,说读出来就是我们自己的,每次考试的考卷都要拿过去给他过目,一看没达到要求,就少不了一顿打骂。我爸对我哥和我姐的要求比较低,因为他们俩都不爱读书,成绩不太好,所以我爸只要求他们及格就好。我姐对读书不感兴趣,到初一就没读了;我哥没考上师范和中专,去莲塘读了高中,但最后还是没考上专科。而我因为成绩一直不错,所以我爸对我的要求也相应提高——每回考试至少80分。以前的80分比现在要难得多,与现在普及性教育不同,那时是以选拔为主的教育方式,“双高”“普九”还没有实行和推广开。
我出生在1971年,正赶上了中国人口出生的高峰期,那时候上学的小孩比较多,交通也没如今发达,有好多地方的人上学比较麻烦、困难,所以当时有个号召,“要把学校办到老百姓的家门口”,以至于一个行政村有好几所小学。比如我所在的大游村有四所小学,大游作为总行政村,在当地建立的小学叫完全小学,有一至六年级(当时为一至五年级),其余三所小学分布在三个自然村,叫村小或民小,最多只办一到三年级。
我小时候周围的读书风气不如现在,大家都不想读书,一二年级班上有四五十人,到了六年级毕业的时候,只有三十人左右了。不想读书的原因和钱有很大关系,我模糊记得一二年级的学费可能是2至3元钱;不过考上万安中学后,录取通知上写着需缴纳学费26元,这我记得清清楚楚——当时看到这个数字我惊呆了,这在那时算是特别贵了,我能将这事记得这么清楚,说明和以往的学费相差极大。
因为小学时候成绩好,我被班主任选为班长,我想老师肯定是把我的成绩和当班长这事写到我的档案里了,(因为)刚进入中学,班主任就说,这人小学是班长,就选你吧。在初中,班长的活比小学要麻烦很多,我们上晚自习的时候,值班老师经常不见了,走之前嘱咐班长把不听话的人名字记下来。上初中后,周围的男生长得特别快,一个比一个高大,我和他们不同,到了初一体重才60斤,又瘦又小,生怕把那群捣蛋的人名字记下来后,被他们揍,我可真打不过他们,所以总管不住纪律。
更让我头疼的是英语课。我小时候比较害羞,害怕讲英语,每回英语老师来上课,进来便直接说英文,还要求班长一定要用英文叫起立。我从前没学过英语,底子差,所以总是不敢叫。后来每次英语老师一进来,我就故意蹲下整理课本。但这样做的次数多了后,也不管用了,老师说这人怎么每次都在整东西,那就稍等一下叫起立吧。我没有办法,班长当了不到一年,就向班主任请辞说不想干了。初中时,教英语的老师也不专业,教我们时用中文拼音的方法,所以我一直对英语提不起兴趣,学不进去,每次英语考试只能照蒙,比如全部打错,或者全部选A,靠这种办法得几分,后来干脆放弃读英语了。
我们那个年代,大家对初中毕业后的去向,选择顺序是“师范好过中专,中专好过高中”。首选师范的原因很简单,农村的学生家里很穷,大家都想早点出来工作,师范是最吃香的,不要交钱,出来就分配工作,可以马上出来为家里分担压力。相比之下,过程最慢且花钱最多的是高中,所以对于我们农村孩子来讲,除了部分家庭条件好的,或者所有科目都学得非常好的,可能会继续读高中去考大学,剩下被迫选择读高中的都是考不上师范或者中专的学生。此外,影响这个选择的还有英语——英语是考高中的必考科目,但是师范录取不计算英语分数,对于英语不好的学生算是最好的选择。
1986年中考时,我背水一战,结果差两分落榜。1987年,我复读一年,英语只考了20分,但是若不计算英语成绩,我在班级排名前五,终于顺利被建阳师范录取。而我的那位同学郭辉,他中考虽然扣除英语外的科目总分没我高,但因为有学英语,顺利考上高中,两年后还被福建师范大学录取,如今在我们县城的中学教体育。万安中学那年有两个毕业班,合起来才三个学生考上建阳师范,其中有个男生和我一样,都是没读好英语而剩下的科目却名列前茅的,而另一个女生的英语还行,但她因为家里穷想早点工作,所以选择把师范放在第一志愿。剩下的同学里,五六个平常有学习英语的同学考上了浦城一中,三个上了中专,那时浦城二中没有招生,县里规定万安乡只能报莲塘中学,所以我们这届还有17人去了莲塘中学,剩下的初中毕业后就没读书了。

1986年,黄小荣(三排左五)在浦城县万安中学的毕业合影
二、师范生走进校园
我读小学的时候,学校和学生都很多,老师却特别稀缺,在农村的小学基本上见不到师范生(出身的公办教师),全是靠民师撑起来的。民师是村里读过书的年轻人,大部分小学或者初中毕业,偶尔也有个别高中毕业的,村里把这些人招来当老师。这些民师的教学质量参差不齐,有好些民师都用方言上课,我们这代人的普通话普遍不标准,与启蒙老师是民师有很大关系。有的民师教学方式比较极端,比如我们村有个人成绩很差,常常不交作业,第二天老师检查的时候,他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于是那民师就用力拉扯他的耳朵教训他,那只耳朵好几次都被拉出了血。

1990年,黄小荣(五排左七)在建阳师范的毕业合影
但我的运气还算可以,遇到的民师不会特别糟糕,而且读三年级的时候就遇到了师范毕业的公办教师。那时候我还不确定他是不是师范毕业的,只是觉得他教书特别规范正式,无论是讲课还是管理学生都很有条理,与以前的老师有明显的不同。他带我们的第一年就赶上全乡期末评比,结果我们考了全乡第一。我小学毕业后,这位老师调到城关实验小学,等几年后我工作,再从同事口中听到他消息时,他已经调到市实验小学了。这是我对师范毕业老师的最初印象,后来初中毕业填志愿的时候,我背水一战选择了师范,一方面是考虑到要挣钱,另一方面自己在那之前确实从未质疑或犹豫过关于成为师范生的这个选择。
1990年,我从建阳师范毕业,被分配到原籍浦城县,县教育局又将我分配到九牧乡。遵从乡学区领导的决定,那年9月,我赴蒋坑小学任教。那年,蒋坑小学包括我在内一共六名老师,除了我之外,其他五名老教师全部是民师出身,其中有三名资历较深的已经转正了,而另外两位三十来岁的年轻民师还没转正。一年后,我又被调到九牧乡杉坊小学,学校有八位老师,情况和我在蒋坑小学时差不多。
那时实际上民师制度已接近废止,师范生陆续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学校也停止向社会招募新的民师。可在农村小学,依旧普遍是学生多老师少,一个老师通常要兼任两个班、两个科目,有时候忙不过来,还会出现一个老师在一间教室同时给两个年级上课的复式班。因此,为了缓解教师短缺的情况,之前招募的民师即便没有转正,还是有好多被保留了下来。
但招募民师这事其实一直没有系统的规范,也不是学校基于整体考虑安排的。我们学校曾经有一位民师,是位校领导的老婆,她因为这层关系一直留在学校。这人只知道最简单的数学列式计算,遇到分数计算,就不懂该怎么通分了,直接分子加分子、分母加分母一通乱算,所以学校只安排她教一年级数学,其他课程她更教不来,也没办法教二三年级。这人的普通话不标准,以前她上课给学生讲数学题,在台上一下子解不出来,于是就用方言对学生说:“你们等一下,我的母鸡要生蛋了,我要去捡蛋。”实际上,她是赶快跑去问她老公,这里该怎么讲。
师范生分配到学校后,或多或少都会成为学校里“扛事”的那位。学区十几位老师都已经中年了,还都是民师转正的,素质普遍不太高。有一次要学区演讲,校长就把这任务交给我。我从来都没有过演讲的经历,有点犹豫,对校长说,我尽量把演讲稿写出来,但讲我肯定不行。校长没答应,说:“现在学校里就你文化最高,你是正宗的师范生,我们这些人都不是,你不去让我们怎么办?”我只能忐忑地接下这个任务,认认真真写了一篇六七页的讲稿拿给校长看,结果他只看了一眼,说:“这个我也看不进去,你按自己弄的准备去就是了。”我没办法,每天早上早早起来背稿子,花了好大的精力将七页的内容背得滚瓜烂熟。比赛那天我发挥得很好,得了一等奖。后来乡里举办建党七十周年知识竞赛,校长又来找我,我担心自己不是党员,去参加这比赛不合适。校长说学校里除了我实在派不出代表了,给了我一堆党史学习资料,于是,我又把所有材料一字不漏地背了下来,跑去参加比赛。最后,我在加时赛中以一分之差遗憾输给来自乡政府的选手,获得第二名。
我们新来的师范生除了在工作上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在生活上也同样也受到了大家的照顾。刚工作那几年,学校的老师除了我之外都是本地人,他们每天傍晚放学都会回家,而我家离九牧乡大约40公里,周一去周六回,所以晚上学校里只留下我一人。刚分配到蒋坑的时候,学校的硬件设施还很差,我的宿舍在一栋泥瓦房中,里面有一张由几块木板简单拼接起来的床、一张桌子、一盏橘黄色的瓦灯,虽然我有心理准备,领导也照顾我是刚毕业的外乡人,将我安排到离国道不是太远的蒋坑村,但是学校的情况还是比想象的荒凉简陋不少。
每周,我都会去乡所在地街道上买回来一点点菜,比如一打海带、一箩筐的芋子,买回来后将它们处理好,摊在屋子里囤积起来,这样一周里我需要吃的菜就有着落了。学校的几位本地老师待我特别好,他们中午在学校打午餐,每天到了饭点就主动来到我宿舍,每人都带过来一两碗家里煮好的菜,加上我自己煮的,大家坐下来一起吃,吃不完的菜他们都会留下来,说我晚上可以吃。虽然都是些普通菜,但从家里带来的总归会比我自己弄的丰盛些,吃饭的人多了也热闹。
当时校长也很照顾我,给我弄来一辆学校的旧自行车,告诉我如果出行不方便的话,可以把这辆车修起来骑,修车花了多少钱拿来报销。不过他还特地交代,不要怎么大修它,这也没法大修了——其实大致的意思是学校没什么经费,大修要花很多钱。有了这辆自行车后,我往返乡镇和村校方便了很多,几年后我又买了摩托车,就这样在九牧高山地区待了近十年。
三、在大山深处的学校
我刚分配那几年,每学期开学初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花大概一个星期时间到学生家里动员孩子上学。1986年国家开始实行义务教育政策,我1990年刚进入工作岗位时,正是这个政策推广的关键阶段。那时在农村,辍学的小孩比例大概达到20%,有些最多读到一二年级就不读了,只读过小学的比例我估计也仅达到百分之七八十。辍学的原因有好多,其中最主要的是家里没钱,交不起学费。
在班级上,上学的男生会普遍比女生多一两个,不过男女生总体的入学比例差别不大,可如果再仔细观察辍学的那部分学生,会发现贫困对于女生辍学的影响可能更大。男生辍学大多是因为调皮爱玩,不想学习了,大部分家庭即便真的很穷,也不会让男生放弃读书去帮家里放牛或者出门打工挣钱;但是我们问女生为什么想辍学,那基本上是因为家里穷。我遇到过一个小女孩,家里虽然很穷,但是她的爸爸妈妈其实是支持她上学的,可是她自己怎么也不愿意去,估计是小姑娘懂事,不想加重家里的负担。我们只能一直对她说,付不起学费没关系,你先来读,学费的事之后再说,可以慢慢交——其实每个期末,都会有部分学生没有交完学费,可一学期也结束了,当时没设立学籍,不交钱对他们几乎没有影响,这事最后总会不了了之。可在开学的时候,我们都不敢对学生说可以不交学费免费来上学。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那里的学费大概是80元左右,如果学生不交,迫于学校的压力,这钱很可能要班主任垫上,而我们的工资就130元左右,80元对于我们来讲不是小数目。当然也有部分老师遇到特别招人喜欢的学生,最后还是会忍不住帮他们这个忙,可是一旦为一个学生开了先例,让其他人知道可以不交学费或者拖到最后老师会帮忙垫付,那其他交不起学费的人很可能会跟风,这事就控制不住了。最后,我们几位老师和一位被动员成功的学生家长一起到这小姑娘家很多次,对他们讲读书好的道理,大家努力动员了好久,这小姑娘才愿意到学校上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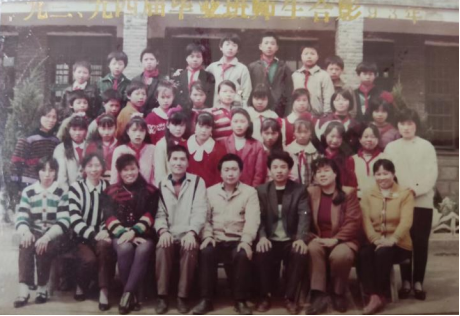
1993年,黄小荣(一排右三)与杉坊小学毕业生合影
以前小学除了设有语文、数学这类常规课程外,还有一门很重要的劳动课,规定每一位学生都必须参与劳动。那时候,学校厨房靠烧柴火来烧水煮饭,这些柴火都是由学生上山砍伐收集来的。每周,学校会安排一个固定的下午作为劳动时间,负责老师分配好任务后,就由学生带着柴刀上山自由行动,每个学生要在傍晚带回规定重量的柴火才算过关。在没有老师看管的情况下,大部分学生都会按时按量自己完成任务,不过也有少数家庭条件较好或者比较宠爱学生的家长拿出家里的柴火帮忙上交。那时候也会发生学生到了傍晚规定时间还没有背着柴火回来的情况,好在最后都是有惊无险,但现在想想,这件事是多危险啊,实在有太多不可想象的不确定因素了,在现在安全第一的理念下是绝对不可能再开展这类活动的。所以大概在2000年之后,类似这样的学生劳动课就没有了。
刚从师范毕业的那十年,我的工作干劲是最足的,教书成绩是最好的,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住校的优势。那时候就我一个老师住学校,一有空就待在教室,然后才是宿舍。我教过小学所有科目,其中最擅长的是教数学。住校的那几年,我每天中午都会到教室,帮学生一对一当面批改和辅导作业,这种方式特别有效,那届学生的成绩在全乡评比中进入前三。那个时期周围老师都在学校打午餐,中午会像我这么做的也不少,所有老师都很认真地抓学生的成绩,这种竞争的氛围给我的感觉特别好。
小学生其实对学习都没有太明确的目的,他们不会真的想到自己需要通过读书出人头地,基本上都不知道自己未来究竟想干什么。所以如果说他们是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好好读书,太不切合实际,那些成绩好的孩子大多也只是明白自己应该要听老师和家长的话,认真学而已。我在杉坊工作时遇到过三名特别聪明乖巧的女学生,其中有个学生叫刘檬,我是她五、六年级的数学老师。这孩子出生在大山深处,虽然家里穷,但是自己争气,学习成绩一直在班级前列,她读五年级的时候,我曾经单独辅导过她做奥数题,还骑摩托车载她到30公里外的城关参加数学竞赛。
学生在毕业后和我们小学老师联系并不多,但这个学生记住我了,后来她考上浦城一中,又被福建医科大学录取,过去通讯不发达,她就经常用写信的方式将自己的这些喜讯和我分享。毕业后,她回到县医院工作,我还找她补了好几次牙。现在,刘檬已离开我们县到福州一所牙科医院担任副院长,成为牙科领域有名的专家,她算是我最自豪的学生。
四、令人羡慕的双职工
我和我老婆是在九牧杉坊小学认识的。我老婆1992年毕业于南平市职业中专,1993年3月被分配到杉坊小学。那时学校里就我们两个刚分配的年轻老师,我们俩都不是九牧乡人,所以每周都同坐一趟班车回家。两个年轻人在一块话题多,聊多了自然也就熟悉了,所以待在一块儿越来越轻松。当时找对象很流行一个词叫作“双职工”,意思是夫妻二人都在事业单位上班,属于拿工资的人。那会儿粮站、银行、卫生院、广电、车站、供销社以及国企是最火热的事业单位,也是在单位工作的人找对象的首选。相比于这些单位的职工,老师属于略被看不起的那类,因为教师的工资比这些单位低太多了,而且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老师还被人称作是“臭老九”,所以那时候女老师都喜欢找在别的单位工作的人。若是按这样的婚姻选择方式,男老师就很难找对象了。

1993年,黄小荣(一排左一)和妻子周兴敏(一排右一)在杉坊小学与同事合影
我是进入师范后才知道这回事。入学开大会的时候,校长在台上说,大家放心,从我们建阳师范毕业的没有一个是打光棍的。他虽然是在鼓励我们,但是听了之后还是不舒服,周围的人也常抱怨当老师工资低,又待在山区,最后可能连老婆都找不到。听多了这种话,我也跟风认同这样的看法,所以开始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抱着考试“60分万岁”的心理,白天常常从教室后门溜出去打球、吃饭、逛街,每天和几个同学七搞八搞,直到考试前一周才躲在餐厅加班加点复习。我们几个还蛮滑头的,带我们班的有一位年轻老师,我们经常跑到他宿舍玩,还老拉他出去和我们一块吃饭喝酒,算是拉拢他,让他给我们些人情分。这样一来,我们的考试才通过。

1987—1990年,黄小荣在福建建阳师范就读时留影
从建阳师范毕业后,真实的状况没我们当时想的那么糟糕,我们几个都陆续找到自己的另一半。不过事实证明,双职工的生活会比单职工的舒适很多。这不是说看不起农村女孩,只是我们的工资普遍不高,当时一个月也就100元左右,如果仅仅靠这一份工资,养活没有工作的老婆孩子一家三口,会过得很拮据、很辛苦。所以当年我想着至少得找个有工作的,结果遇上了我老婆。她也是这么想的,觉得我还可以,鼻子蛮大的,就是眼睛小了点。她还说过不要抽烟的,我到现在为止也没有抽过一根烟。
谁也没想到,仅仅过了十来年,当年那些看不起老师的人就都后悔了,粮站、供销社早已撤出,车站、广电部门渐渐衰落,国企职工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陆续下岗,只有银行、卫生院还勉强维持着。近十多年来,我开始听到好多人说,还是羡慕两个老师的组合。我和我老婆是自由恋爱,我老婆分配到学校后,我们俩很快就在学校两位老教师的撮合下在一起了。我们的父母对我们结婚没什么要求,一切都由着我们自己计划,于是很快我们就开始为结婚存钱了。1993年,我的工资大概有140元,和刚工作的时候差别不大,我每个月只需要三四十供日常花销,然后把剩下的100元都存起来。等到1997年我结婚时,我的工资涨到了700元。
那几年开始流行大彩电,一台“大屁股”电视要2000多元,DVD是高档用品的代表,加上音响要1000多元,村子里只有非常少的几户条件好的人家里拥有它们,我想既然是结婚,那一定得买彩电、DVD。我们都在40公里外的九牧乡上班,所以自行车也是必需的了,几年后又开始流行摩托车,比自行车更高档些,另外冰箱、液化灶也都是结婚后的生活必需品,所以我们把这些都列入了结婚必需品里。两个人一起存了大概五六千才将这些东西买齐。学校对老师的婚姻不会有较多的干涉,不过一旦谁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就会马上让他离职。我们结婚时,先要让学校查看我们身份证上的年龄是否达到22岁,达到了才会给我们开证明,带着这份证明才能领到结婚证。我1997年11月1日结婚,那年我26岁,对于那个年代的普通人来说,已经属于晚婚了。
1999年,我们的女儿出生时,我和我老婆已经调离九牧乡,来到家庭所在地万安乡工作。为了方便带孩子,我们提前一年把孩子带到学区中心小学,让她尝试着读一年级,我老婆在中心小学上班,正好可以照顾她。女儿坐在班上,我们见她挺乖的,虽然还不足龄,但能跟上老师教的内容,所以就这么将她升上去了。女儿在我们学区中小读到二年级,三年级是小学课程的转折点,她要开始接触英语了,我们决定将她转到城关小学。关于女儿到城关上学这事,我们在几年前就已经计划了。2003年,女儿刚进幼儿园时,我们在城关贷款买了商品房,房价加上装修在11万左右,我们两个工资合起来一个月大概1600元,每个月还500元贷款,还需要存部分钱用来还买房时借的两万元,剩下的再供三个人生活。所以,刚买完房的那几年,我们一家经济压力挺大的。
如今快二十年过去,女儿早已先后从城关的第二中学、第一中学毕业,现在研究生在读,虽然不是最顶尖的高校,但本硕都算是国内的重点大学。在老家村子,她是同一批长大的孩子里在学业方面最优秀的,这让我们感到欣慰。在我身边,职工子女考上好大学的比例远远高于其他群体,农民的孩子也有出人头地的,但是这类情况非常少。我觉得这样的结果受地域的影响并不大:这些年,国家已经为农民子女的教育创造了很好的条件,至少在我所在县域内,城关小学和乡村中心小学的教学条件相差已经不是很大了。现在很多农民选择外出打工经商,挣了钱后大多都会往子女教育这块砸钱,他们的孩子在教育资源这块,已经和城里出生的孩子差距不大了。以农民为代表的非职工人员的子女学习成绩之所以偏低,在我看来,一是农民大部分自己文化水平低,没有能力教孩子学习;二是农民没有时间更没有花精力认真抓孩子学习。并不是说让孩子在某个很好的学校读书,上特别贵的补习班,成绩就可以上去,有时候家长给孩子的条件越好,比如为他们配上各种高档电子设备学习,孩子就越爱玩,小孩子不懂事,哪里会珍惜?但对朝九晚五的职工来说,我们可能会把很大一部分的时间和精力花在辅导小孩学习上,这便产生差距了。过去十几年,农村百分之七八十的父母对孩子的教育问题还是挺重视的,都会积极送小孩去上学,但总有一部分家长不重视这件事,觉得上学不仅要花很多钱,而且起不了很大的作用,有些人没上学最后也能吃饱、喝饱、赚大钱,而那些上学的人还是当个穷教师,拿一点点工资而已。
近年来,农村的待遇渐渐提高,但农村教师和村民的关系并没有因此得到改善。我刚毕业那会儿,虽然老师的待遇很低,但由于扫盲、夜校农机教育等等的缘由,我们经常入户和村民打交道,所以老师和村里的联系得挺紧密的。村民对老师也挺热情,每年教师节,村委会都会拿几百元请我们聚餐,剩下的钱再为每个人买个纪念品。但现在,老师和村里几乎没有联系了,除了在学校上课外,我们没有参与村里的任何事情,村民们也觉得老师是县里派来的,我们拿着国家工资,理所当然为农村教育做贡献,我能感受到我们和村民因为距离问题导致的人情疏远。反而是乡政府更照顾我们,去年教师节乡政府给学校发了5000元,用来给我们一个人分一张100元的购物卡,以前没发钱的时候,还会发雨伞、热水瓶、折叠椅、不锈钢餐具等。所以,乡村教师这身份绝对说不上好,但也不能算差。
五、新的乡村教育工作
大概从1995年开始,我们县各乡镇的村小、完小就陆续被撤销。这么做一是因为大部分农村孩子都进入城关小学就读了,我们县城关近几年不断扩大招生规模,面向全县放开招生,农村孩子靠摇号就可能进入城关小学读书,去年万安乡因为完小撤除而无法在本村就读的几个学生,最后全部靠摇号进入城关小学。二是因为县城小学的总体生源减少了,由于早些年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现在的小学生都是独生子女的子辈,加上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全县中小学学生数量大概在两万左右,在读学生人数最多的时候,也只有我刚工作那会儿的二分之一。
相较于城关小学,农村小学生源的流失更加严重,2001年我到万安乡任教时,全学区有一千多名学生,如今不到300人,是20年前的四分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首先被撤除的是位于最偏远农村的村小、完小。这类学校人数本就不多,我刚工作那会,蒋坑小学只有50名学生,后来我调任到万安乡的各村小、完小工作时,学校学生人数都在100左右,之后生源逐年减少,到2005年大规模撤除点时,部分村小、完小的学生人数不足30人。可这么点学生却分布在六个年级中,这样的情况下学区该为这所学校分配几位老师合适呢?这让学区很犯难,所以必须做出改变,减少底下学校老师的数量。到现在,一个中心小学加一个行政村完小基本成为乡镇小学的标配。不过也有例外:村小完小的合并需要各村百姓点头合作完成,而位于县城边界高山地区的盘亭乡,因为当地百姓不愿意合作,所以至今还保留着好几所村小、完小。
与“普九”时期大规模建校相比,农村小学撤点集中办学集中了资源,除了因此改善农村的办学条件外,也能凭此最大限度利用好有限的教师资源。学校生源减少后,农村不再面临老师短缺问题,学校也不再请代课老师了,所有在岗教师几乎都在编制内。现在老师很少有直接分配的,大多数都是靠招考进来,参与教师招聘的也不一定是师范生,都是些普通本科、大专毕业生。几乎没有名牌大学毕业生会来小县城的农村小学当老师,我们学区近十年的新进老师里,条件最好的是一位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的女生。她2013年毕业,报考了我们县的乡村教师招聘,上岗后学校安排她先到村小交流三年,直到中心幼儿园原来园长调离后,她才从小学重新回到学区幼儿园,还接任了园长职务,直到现在。而随着村小、完小的撤除,和我一样原来在村小、完小工作的老师也都陆续被调回中心小学工作。

2021年,黄小荣重走九牧洋墩小学,当年的教学楼早已荒废
如今老师的调动基本也只能发生在乡镇范围内。1997年,我们县的教师被纳入编制,在全县范围内设定教师编制的总数。但在2007年,编制发生改革,改为每个单位的编制是固定的,同时工资与编制密切关联,一旦工作发生调动,原有编制下的职称关系无法随着工作地点一起变动。除非新工作单位有对应的职称空缺,或者原工作单位愿意为他保留职称关系,否则一切就得从头开始。所以现在除了副校长因为工作需要可以带着职称关系经常变动外,普通的教师原则上都不能再随意调动到除本乡镇之外的其他学校,一旦报考教师时选择到乡镇学校工作,就很难再进城了。
以前,我们老师都比较羡慕在教育局工作的人,他们整天坐在办公室里,不用上课,手里有权,给人一种荣誉感。但是后来教育系统的权力往上级部门收紧,教育局下面各股室的办公人员,都和我们一样,只是干活而已。现在乡镇小学的校舍基本已经全部翻新,学校配备了标准的美术室、音乐室、体育活动场所等,一切都向城市学校建设的标准对齐。我所在的万安乡又是离城关最近的乡镇,每天上班开车仅需要15分钟,与去城关边缘位置小学需要的时间其实差不多,所以对我来说,在乡镇和城关工作的体验感基本没有差异了。
从2017年开始,福建省还设立了乡村教师补贴的专项经费,根据乡镇离县城的远近发放补贴,多的一年合计有近万元,是一笔很大的额外收入。不过与公务员相比,教师的收入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国家出台政策规定“教师工资不得低于当地公务员工资”,但这个说法仅仅体现在基本工资表上的总额一致,公务员的各类奖金补贴比教师还是高出不少的,可能我们年收入只有七八万,但同一地区的公务员达到十来万了。
大概五年前,我曾有个机会可以被借调到教育局工作。那时候我是学校的教导处副主任,负责学校所有排课事务,而我老婆正处于癌症术后化疗康复的关键阶段,学校领导在综合考虑后决定给予她特殊照顾,一周只安排了几节课。这事招来部分同事眼红,每回我排代课,有些人就会回我:“我们可不像某些人哦,一周只需要上几节课……”“让你老婆去代……”,以我老婆的事来抗拒我的安排。我干得很憋屈,就想要换个环境,刚好一个领导告诉我局里有个股室有空缺,股室领导问我是否愿意去。这事我犹豫了两天,没有去主动争取,结果这岗位马上被其他人占去了,我没去成。不过现在想想,这事也没什么后悔的。那时学校的原总务处主任也要退休了,我很快就离开教导处,去填补总务处主任的位置。这份新工作不再整天和人打交道,负责学校的财务、后勤类工作,事情很烦琐,但是我干起来舒服多了,刚好我是比较喜欢业务工作的。
我年轻的时候,曾经羡慕过那些通过赛课进城或者被借调到政府部门工作的同事,也曾经尝试过到福州的私立学校应聘,但最终都因觉得自己不合适那样的工作环境和工作内容告终。如今,随着乡村教育工作环境的改善和年岁的增长,我再没有想过要离开这个岗位。如今,乡村教师虽然地位不能算高,但算得上是幸福感和舒适度较高的职业了。
教育给我最大的影响就是,让我摆脱了农民的身份,而对现在的乡村孩子来说,他们拥有比我们那个年代更好的机会。我不太赞同“寒门难出贵子”这说法,因为现在的教学条件普遍上差别已经不是很大了,真正造成差距可能是教育方式和课后陪护问题。我也不太认同“寒门(易)出贵子”,这更多是一个概率问题,可能上千户贫困家庭仅会出一个优秀的孩子。在我看来,乡村教育还需要坚持,要把擅长或不擅长读书的人都培养出来,有能力读书的继续读好书上大学,学习能力偏弱的上职业学校,毕业后依然能够成为建设祖国的栋梁。在农村孩子接受教育的最初阶段,想办法培养好这群孩子的基本能力,就是我们能做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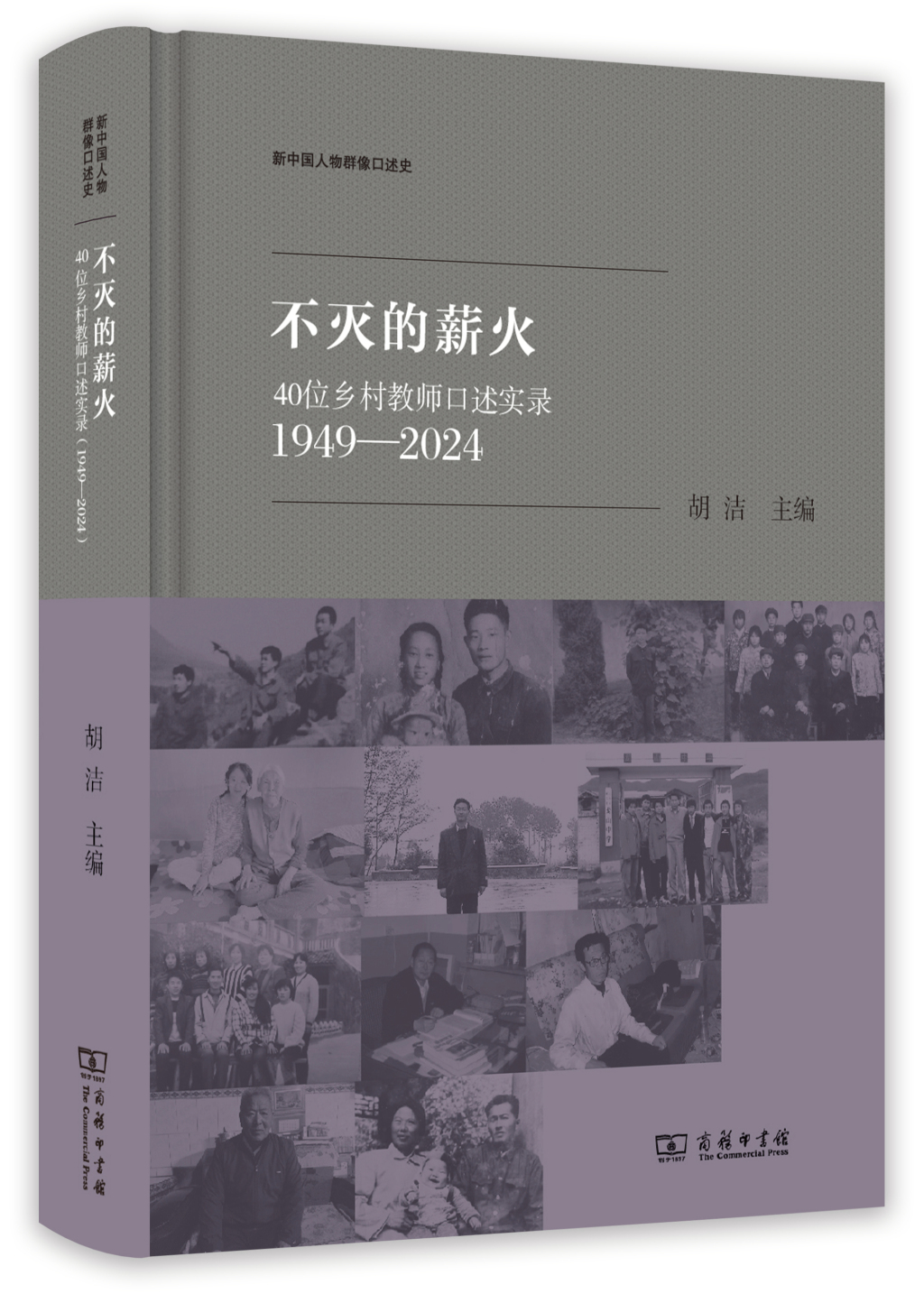
本文选摘自《不灭的薪火:40位乡村教师口述实录(1949—2024)》,胡洁主编,商务印书馆2024年12月出版。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