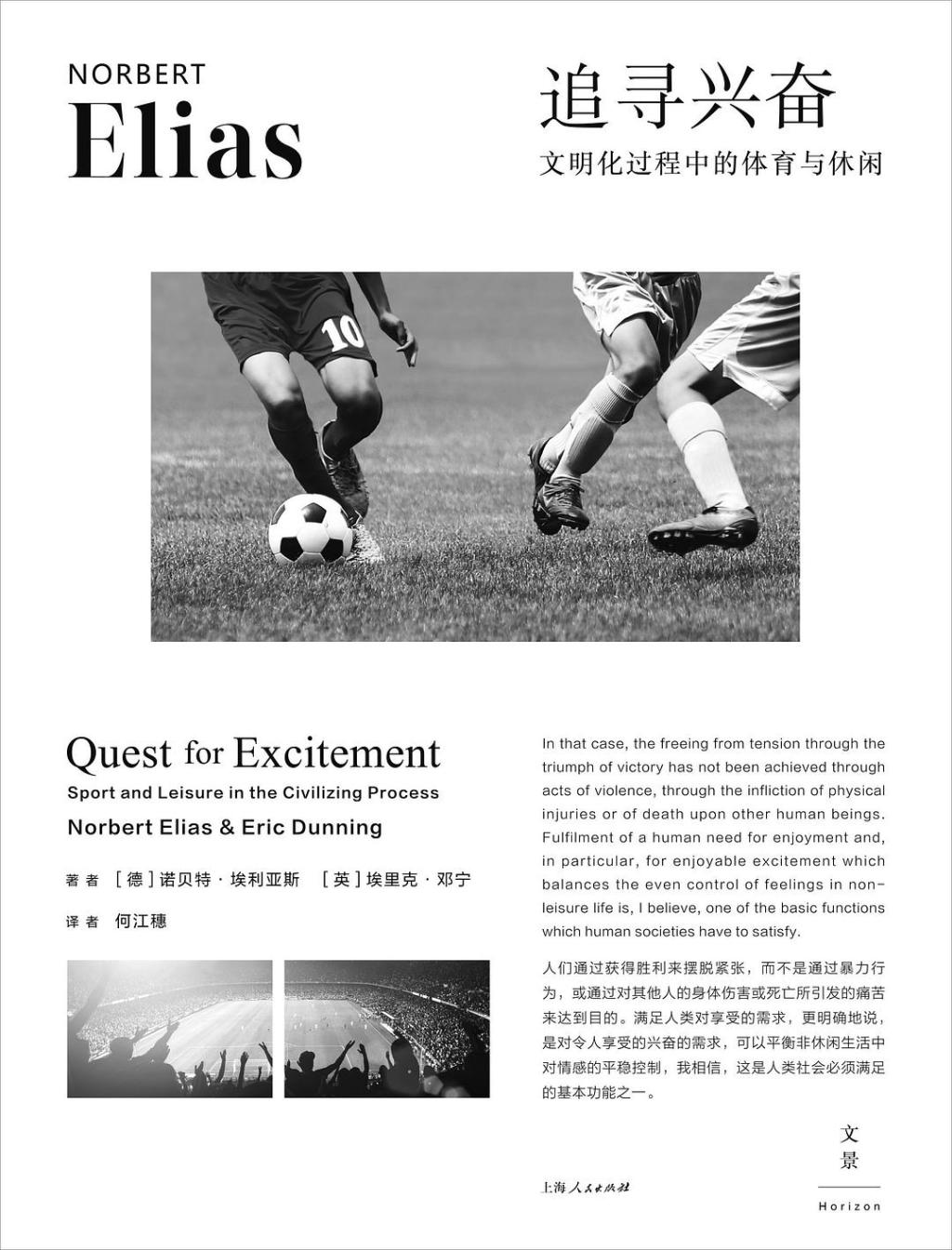
《追寻兴奋:文明化过程中的体育与休闲》,[德]诺贝特·埃利亚斯 / [英]埃里克·邓宁著,何江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丨世纪文景,2025年4月版,416页,95.00元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1897-1990)与他的学生、英国社会学家埃里克·邓宁(Eric Dunning,1936-2019)合著的《追寻兴奋:文明化过程中的体育与休闲》(Quest for Excitement: Sport and Leisure in the Civilizing Process,1986;何江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4月)是体育社会学重要著作。
本书译者认为,书中文章的研究对象虽然都是摔跤、猎狐、足球、足球流氓、拉格比球之类,如本书主标题所讲的“追寻兴奋”,但文章的研究主题却如副标题所示,是关于文明化过程的探讨。具体而言这些文章大体上是围绕两个论题来展开:其一,参与及观看体育运动是对兴奋的追寻,是对在文明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例行化的工作及生活的应对;其二,体育运动经历了从直接的身体暴力向模拟打斗的转型,其发展是与社会整体的文明化状况紧密相关的。“总的来说,以体育运动为研究对象的这本文集,并不应简单归在体育社会学这个研究类别之下,而应视为对‘文明化过程’‘型构’等埃利亚斯社会学理论中的关键概念的阐述和扩展。”(译后记,406-407页)这一理解是对的,因为埃里克·邓宁在本书“前言”中就指出这些文章都是埃利亚斯关于文明化过程及国家形成的开创性研究的系统中发展出来的,是对这一理论及研究体系的例证和补充,也是埃利亚斯所提出的独特的社会学“型构”及“发展”取向(figurational anddevelopmental qpproach)的代表(3页)。
该书是一部主要发表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晚期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的关于体育运动及休闲研究的论文合集,作者除了诺贝特·埃利亚斯和他的学生、英国莱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埃里克之外,作为第九章的那篇论文是邓宁和另外两位合作者撰写的。在1986年结集出版的时候,收入了邓宁撰写的“前言”和埃利亚斯撰写的“导言”,实际上这是两篇关于体育社会学的长篇论文。全书共十章,都是原先发表过的论文,有些在收入本书时作了修订。这十章的题目分别是:“在休闲中追寻兴奋”“业余时间光谱中的休闲”“作为社会学难题的体育运动生成”“关于体育运动与暴力的论文”“中世纪及现代早期英国的民间足球”“体育运动群体的动态机制,特别是关于足球”“现代体育运动的动态机制:对成就—努力以及体育运动的社会意义的讨论”“体育运动中的社会纽带与暴力”“足球比赛中的观众暴力:迈向一个社会学的解释”“体育运动作为男性的保留地:关于男性特质认同及其转型的社会渊源的讨论”。可以看出,这些论文以“体育”和“休闲”为主要线索,从社会学的角度分别对体育运动的兴奋来源、业余时间光谱、足球运动的发展演变、体育运动中的暴力与社会纽带、体育运动与男性气质等议题进行探索性的研究。在研究中,埃利亚斯的经典理论“文明化过程”是贯穿在各种研究议题中的核心概念,是“文明化过程”理论对于发展中的社会学研究领域具有深远影响的又一重要例证和学术成果。另外可以看到,被称作体育社会学先驱的埃里克·邓宁作为埃利亚斯的学生和学术上的重要合作者,他的贡献也是非常突出的。因此,诺贝特·埃利亚斯在“导言”特别提到“这本书中的一些部分是埃里克·邓宁和我合作的成果。这一合作持续了几年,我很享受。现在这次合作的成果第一次结集成一本文集,埃里克·邓宁自己的研究极大地提升了这本合集的质量”(30页)。
埃里克·邓宁在本书的“致谢”谈到他的老师诺贝特·埃利亚斯给予他的巨大帮助,讲到了五六十年代的社会学研究的状况:“当时,社会学这个研究类别在很大程度上陷于毫无生机的僵局,理论上以功能论的静态形式为特征,经验上也是以同样静止且乏味的实证主义形式为特征。”(1页)他在“前言”中继续谈到了对体育社会学的发展状况的看法,在此我们应该简单回顾一下这个学科的起源。
从起源角度来看,英国学者、社会学创始人之一H.斯宾塞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就探讨过体育的教育问题,德国社会学家M.韦伯论述过清教徒对体育运动的兴趣,G.齐美尔也曾以体育竞赛来揭示人的社会化,并把它视为冲突中的一个统一因素。一般认为在1912年出版《运动社会学》的德国学者H.里塞和在1937年发表《体育社会学》的美国学者F.罗德是现代体育社会学学科的开拓者,初期的体育社会学侧重研究竞技、体育团体、大学体育运动、观众等问题。二战之后,美国、波兰、日本、苏联、芬兰等国的学者对体育运动进行了系统的社会学研究。1956年罗德等人发表的《目标──建立一门体育运动社会学》一书被公认为体育社会学的首创性著作。1964年 6月,在国际运动与体育理事会日内瓦工作会议上正式成立国际体育运动社会学委员会,组织举办年会、世界性学术讨论会以及编辑出版《国际体育社会学评论》等刊物。此后不久,国际体育运动社会学委员会被国际社会学学会接纳为会员,标志着体育社会学学科地位的正式确立。另外不能忘记的是,约翰·赫伊津哈的《游戏的人》和托尔斯坦·凡勃仑的《有闲阶层理论》就是最早以更普遍的方式思考体育的著作,它们都为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兴起作出了贡献(https://zh.wikipedia.org/wiki/体育运动学)。
埃里克·邓宁在该书的“前言”中认为,体育社会学直到相当晚近才被作为一个专门的领域,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开始,体育社会学的发展就不再那么薄弱了。但是就它目前的状况来看,体育社会学仍然主要是体育教育家们的创造,他们的研究既缺乏对有成效的社会学分析来说所必需的一定程度的疏离,同时还缺乏所谓对社会学中心关怀的“有机”嵌入,即未能从有关体育的研究中展示更广泛的社会关联。因此他说“我确信多数社会学家都会赞同:到目前为止,体育社会学中的多数研究不大可能激发体育教育领域之外的兴趣,也不大可能吸引‘主流’社会学家的注意。”(4-5页)
实际上,在古典社会学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到一种不断拓展的、开放的、宏观的研究视野,例如从杜尔凯姆研究的社会分工、教育、宗教、自杀等到韦伯研究新教精神、工作伦理、世界经济史、统治形态、世界几大宗教,从齐美尔开创了冲突论、交换论、符号互动论等研究到埃利亚斯研究文明进程、权力、知识社会学、宫廷礼仪、音乐家莫扎特、体育,可以说明在社会学奠基人的心目中,社会学不应该成为一块被固化的、越来越“专业化”的学术园地。以“历史社会学”(historical sociology)为例,正如E.H.卡尔说的:“历史学变得越来越社会学化,社会学变得越来越历史学化,这样对两者都有更多的益处。让社会学、历史学之间的边界保持更加广阔的开放态势,以便双向沟通。”(E.H.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161页)这种双向的学科化使学科边界保持开放性,这是复合型学科的特征与优势。但是,历史社会学的基本问题意识仍然落脚在社会学问题之上。英国历史社会学家丹尼斯·史密斯(Dennis Smith)认为,“历史社会学是对过去进行研究,目的在于探寻社会是如何运作与变迁的。”(丹尼斯·史密斯《历史社会学的兴起》,周辉荣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4页)因此从严格的学科分类来说,“历史社会学”仍然被认为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分支。这对于认识体育社会学的学科属性与研究领域很有启发性和参考价值,也是理解埃利亚斯和邓宁为何坚持把体育社会学视作社会学研究分支的重要参照。
如何更为深入、更有成效地把体育研究与社会学紧密结合起来,正是这部《追寻兴奋:文明化过程中的体育与休闲》收入的各篇论文从不同的研究议题所共同指向的目标。如果以“追寻兴奋”这个核心概念来描述这种学术探索的过程,也是恰当的——正如埃利亚斯在本书导言中所讲的:“追踪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看起来不言自明的制度的起源及发展,本身就是一项令人兴奋且很有价值做的工作。”(50页)
埃利亚斯在“导言”和《关于体育运动与暴力的论文》中比较集中地论述了体育运动与十八世纪英格兰宪政的关系,这是在“文明化过程”中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论题,是把体育运动学与政治制度史研究紧密联系起来的重要研究案例。问题是这样提出的:为什么游戏-比赛的文明化以及通过社会规则限制针对他人的暴力行为会首先在英格兰发展起来?体育运动为什么首先出现在十八世纪英格兰上层社会?(36页)埃利亚斯认为,这种相对非暴力类型的体育运动的出现,与社会整体的发展有关:暴力循环有所缓和,解决冲突利益或信仰的方式是“允许政府权力的两个竞赛者完全通过非暴力手段,并按照双方共同商定的、遵守的规则来解决他们的差异”(39页)。在这里就呈现出英格兰议会政体与体育比赛的之间的某种亲和力,这种亲和不是偶然的,而都是因为在不同领域中出现“文明化过程”而产生的。
在十八世纪的英格兰,狩猎、拳击、赛马和一些球类运动等特定类型的休闲活动具有了体育运动的特征;而“当议会政体在18世纪出现于英格兰时,其主要要求是:如果在议会的一次重要投票或者整个社会的选举中失利,政府中的派别或党派就有遵守议会游戏规则的要求,准备好将权力移交给对手,而不使用暴力。”(41页)因此他指出:“议会制政府的出现,作为英格兰国家形成过程——具体地说,是国王与有土地的上等阶层之间的权力平衡的转换过程——的一部分,在英格兰社会的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而不仅仅是从属性的作用。如果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体育运动形式的消遣在英格兰发展起来了?那么回答时就不能忽略议会制政府的发展,还有因此或多或少自治的贵族及乡绅的发展,这些对体育运动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49页)可以说,英式议会政体与英式体育运动在十八世纪的出现是相互作用的“文明化过程”的结果。
在议会政体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对待使用暴力的态度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埃利亚斯指出:“议会政体的逐步建立,代表了非常明显的和缓化的迸发。这要求更高水平的自我约束。这种自我约束是必要的,只有所有相关组合都坚定地放弃了使用暴力,根据协商一致的规则,自己的对手才可能上台并享受其果实及权力资源。有产阶级相对更暴力且管制不够得当的消遣活动,现在转化为了相对不那么暴力且管制得更细致的消遣,这几乎不是偶然,这些消遣将现代含义赋予了‘体育运动’这个表达。在同一时期,正是这些社会阶层开始宣布放弃暴力,并学会了自我约束的强化形式,而这是议会形式的控制,尤其是议会形式的政府轮换所要求的。事实上,议会竞争本身并非完全缺乏体育运动的特征,以言辞为主的议会争斗也并不缺乏令人享受的紧张-兴奋的机会。换句话说, 18世纪英格兰政体的发展及其结构,与同一时期英格兰社会上层消遣活动的体育运动化之间存在很明显的密切关系。”(238页)这段论述把议会政体的建立与体育运动的发展中共享的节点讲得很清楚:那就是对待使用暴力的态度和立场。应该说,这就是“文明化过程”中的产物。
说到底,英式议会制度就是要通过遵守大家认同的规则打破暴力循环,实现对权力和利益的制衡。既要维持对国家权力的控制,又要防止暴力的行为,就要求认真地权衡和要有妥协的准备。埃利亚斯指出:“议会政体在18世纪的发展,是对这类权力平衡的回应,这样的权力平衡确保了英格兰国王没有像法国国王那样,英格兰国王永远不会将上层精英转化为朝臣,也不会恣意侵犯他们的利益。……英格兰传统的等级会议转化是制度性的变化,也显示了英格兰上等阶层人格结构的变化。这种未经计划的发展,使得英格兰有土地的上等阶层能够击败所有建立君主专制政体的企图……”(52页)国王不能把上层精英变为自己的朝臣,也无法为自己建立君主专制政体,这就是对国王权力的根本性制衡。看看今天美国政坛的种种乱象,实在令人感慨的恰好就是白宫内的“朝臣”现象和总统权力朝向专制化步步迈进的危险。
想起多年前读过的英国宪法学家阿尔伯特·维恩·戴雪(A. V. Dicey,1835-1922)的名著《英宪精义》(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1885;雷宾南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该书早在1935年就由商务印书馆刊行,译者雷宾南是民国著名翻译家、教育家,该译本译、释并重,但其用语、行文时有“艰奥、迂曲”之处。前几年出了新的中译本,书名改为《英国宪法研究导论》(何永红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9月)。戴雪被认为是英国宪法的编纂者,甚至有现代英国的“Founding Farther”之称。深受震撼的是他在这部著作中对“英宪”(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宪法”)的阐释,从中看到自由生成与不成文的“软精神”在平衡与维护自由、权利与传统中的巨大力量。这也正是埃利亚斯所强调的英式体育运动与英格兰议会制度起源的共同点:自由生成的“软精神”,维护自由与权力的平衡。另外还有英国著名法学家弗雷德里克·威廉·梅特兰(Frederic Willian Maitland,1850-1906)的《英格兰宪政史:梅特兰专题讲义》(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1908;李红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即便是对于英格兰宪政的历史素无研究,在阅读中也能了解到自1215年约翰王(John,1166-1216)不得不签署了《大宪章》(Magna Carta)以来,英格兰的统治权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在国王、贵族和议会之间调整配置的历史。不过,无论是戴雪还是梅特兰,他们都没有把十八世纪的英式体育和休闲活动与议会发展的历史联系起来。
埃利亚斯在论述英国议会和上层社会的时候,经常与法国的情况作对比,他指出:“在法国,由于国王的至高无上和统治形式的君主专制,派别之间的分歧及斗争通常并不被允许公开化。而在英格兰,议会政体不仅允许对立派别之间公开竞赛,而且使得这种公开做法成为必需(necessary)。在议会社会中,社会生存以及最确定的社会成功,都有赖于争斗的能力.但并不是使用匕首和剑的争斗,而是运用论证的力量、说服的技能和妥协的艺术……我们可以看到议会竞赛与体育运动竞赛之间的亲和性。后者也是竞争式的斗争,绅士们在这里不使用暴力,或者在诸如赛马或拳击之类的观赏型体育运动中,则尽可能地努力消除或缓和暴力。”(53页)这里再次对何谓“文明化过程”作出了形象的阐释。这也就看得比较清楚了。有些宪法学家没有看到或者并不重视体育运动与议会制度的实施与发展的关系,可能是因为受学科分隔的学术体制的影响,而社会学的传统如前所述,有利于发展出更为开阔和跨学科的研究视野。
但是,在把体育运动发展与议会政治的发展联系起来的时候,埃利亚斯的研究态度还是比较审慎的。对于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他不认为有什么事件是注定(bound)会出现的。对于社会不同领域之间的发展的关联,他认为:“在这个个案中,是上层阶级议会式的统治方式与上层阶级以体育运动为形式的消遣之间的关联,这些关联并不具有因果(causal)关联的特征。可以简单说,参与了议会派系竞赛的和缓化以及更大程度的规范化的这群人,在其消遣的更大程度的和缓化及规范化中起了重要作用。但不能认为在这一个案中,英格兰古老的上议院及下议院的议会化是原因,而体育运动是它的结果。当体育运动和议会在18世纪出现时,它们既是英格兰权力结构变化的特征,也是因之前的斗争而成为统治群体的那个阶级的社会惯习同步变化的特征。”(57页)两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但重要的是参与这两种活动的人基本上是同一个群体,都是处在社会惯习同步变化中的人群,这就是“文明化过程”中的人与社会惯习的相互形塑。
谈到体育运动与社会公共领域可能存在的关联,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一些个体经验。我想起在“文革”后期读中学的时候,曾经对一位班主任选择男生干部的方法印象深刻。与其他老师主要以“根正苗红”(家庭出身好)和“听话”“敢于向坏人坏事作斗争”等标准不同,这位班主任却选喜欢体育运动、在球场上有威信、最好是队长之类的男生,只要他的学习成绩还可以,那就是他了。后来发现,让这样的男生当“副班长”,配合女生“班长”执行老师安排的工作,是很好的搭档。老师需要的不仅是听话的学生干部,更需要的是需要其他同学愿意听他的话的干部,而小伙伴们中间的球队队长就是最佳人选,即便在旁人看起来他不是很听话。而且,永远听话的孩子只要有一次不那么听话,就会被老师批评;而平常不怎么听话的,只要有一次表现好一些,老师就会大大地表扬,选他做班干部就有示范效应。把这些记忆中的学生政治放在埃利亚斯和邓宁他们的体育社会学中不仅不违和,而且是一个有意思的微观论证:体育运动中的竞争与建立威信的过程可以对管理学产生直接的作用和正面的意义。另外还有一个经验也是与我读中学那个时代有关。尽管“文革”后期的中小学教育很重视体育课,那首“运动员进行曲”整天回响在耳边,但是关于普世的体育精神却是从课本上收入的鲁迅文章《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才从反面接触到,老师讲解课文的时候总要先解释什么是“费厄泼赖”,然后才是为什么要痛打“落水狗”。忘记老师当时具体怎么解释的,总之就是体育比赛要守规矩、要用正当手段之类。问题是,如果今天还在讲这篇课文——我想应该没有了,是否可以讲到英国人以体育运动的fair play原则运用于政治党派之间斗争和社会生活中去?再后来,在大学二年级学习十九世纪政治史的时候,与“议会道路”并提的必然是“暴力革命”,前者当然是要被彻底批判的对象。
多年前我曾经为现代奥运会之父皮埃尔·德·顾拜旦(Pierre de Coubertin 1863-1937)的侄孙诺佛瑞·德钠瓦塞尔·德·顾拜旦男爵的《“奥运之父”顾拜旦的一生》(王益群译,南方日报出版社,2008年5月)写过一篇序言《学习一种人生哲学》,文中谈到了在顾拜旦的奥林匹克理想中,英国绅士的价值观念与传统占据重要的位置;还谈到了在他创作的散文诗《体育颂》中充满的对社会正义与公平的理想,并由此反思体育在国民性格改造中的意义。以上这些个体经验都可以作为体育运动与社会各方面生活的广泛联系的微观例子,可以说明即便处在非常特殊的时代语境中,体育作为人类生活的基本生活必然要在埃利亚斯所讲的“人作为个体”与“人作为社会”之间的互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内容中,埃利亚斯反复论述的英格兰议会政体是一个重要的对象。1876年出任大清国驻英国公使的郭嵩焘(1818-1891)很有可能是在近代史上最早认真考察了英国议会制度的中国人。他在光绪四年(1878年)二月三十日应邀赴下议院听会,回来后在当天日记中记录了会议上议员相互诘问辩驳的情形(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出版社,1984年11月,159-160页)。在十一月十六日的日记中更是谈到了新闻与议会的议论、辩驳情况:“西洋一切情事,皆著之新报。议论得失,互相驳辨,皆资新报传布。执政亦稍据其所言自由之得失以资考证,而行止一由所隶衙门处分,不以人言为进退也。所行或有违忤,议院群起攻之,则亦无以自立,故无敢有恣意妄为者。当事任其成败,而议论是非则一付之公论。”(同上书,401-402页)在十二月十四日的日记中又写着:“两党之势既定,议论同异,相持不下。大率当国者议论行事足以相服,则亦转而从之。其初各以其党持议,几于一成而不可易。盖军国大事一归议院,随声附和,并为一谈,则弊滋并多。故自二百年前即设为朝党、野党,使各以所见相持争胜,而因剂之以平,其由来亦久矣。”(429页)是月十八日又记:“自始设立议政院,即分同、异二党,使各竭其志意,推究辨驳,以定是非,而秉政者亦于其间迭起以争胜。……世安有无政治教化而能成风俗者哉?西洋一隅为天地之精英所聚,良有由然也。”(434页)以上所引,恰可与埃利亚斯的论述相印证,而且他最后提到的教化、风俗和精英问题,也和埃利亚斯的“文明化过程”相联系。郭嵩焘回国后,把伦敦日记整理为《使西日记》印行,却激起满朝官员的公愤,以致“奉旨毁板”。他本人亦不再被起用,直至光绪十七年(1891年)病卒。郭嵩焘生活的年代当然难以容下他对在英国所见所闻的思考与传播,但是历史的回音并没有随着“毁板”而消失。
最后要回到一个问题:在当今的全球化世界中,政治制度与体育运动相契合的那种“文明化过程”还能朝着进步的方向发展吗?邓宁在“前言”中说过,埃利亚斯的文明化过程理论有时候会被诠释为指称一个简单的、单线的、进步的且不可逆的趋势,他当然不同意这样的看法(23页)。埃利亚斯自己在“导言”中提醒我们要警惕这样一种情况:“文明化过程和其他在特定方向上的社会变化序列一样,可以倒挡后退。文明化过程可能会跟随‘去文明化’的过程,甚至可能朝着相反方向的迸发。”(64页)他以假设的论述方法描绘了一面我们今天已经不会太陌生的社会镜像:“如果部分人口稳定的自我控制能力减弱了,如果暴力经由自我升级循环使人们避免实施暴力行为的意识衰退了,那么议会政府也会衰弱。如果人口的不同部分之间的敌意及仇恨上升到一定水平,按照既定规则进行的和平的政府轮换,也就不再能够正常进行。”(76-77页)
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学家真的没有理由忽视研究体育运动所具有的社会学意义;而从事议会制度研究的学者也应该从体育社会学研究中获得有效的观察角度和思考方法。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