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汉朝人司马迁来到B大历史系求职,递交了著述《太史公书》。据说,经过学术委员会的认真审查,结论是可以聘为文员,到图书室整理资料。理由干脆利落,此公没有发表过一篇学术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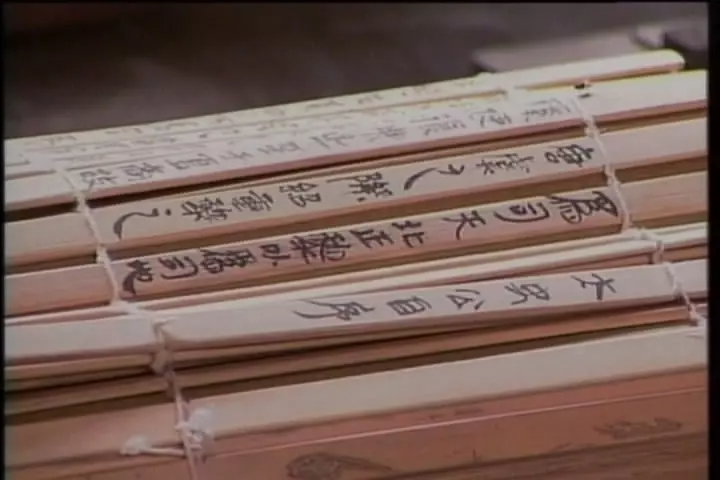
《太史公自序》竹简。图片来自三联书店公号
这个看似荒诞的“思想实验”,正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今年7月出版的新书《司马迁来到B大历史系》中,抛出的一个深刻而尖锐的问题:
当《史记》只能被归为“研究资料”,当研究《史记》的教授凭借“史记研究之研究”名满天下,司马迁本人却只配做图书管理员时——我们是否正在失去太史公“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宏大叙事能力?当下,当历史学日益萎缩在论文的象牙塔中时,我们是否还能找回那个让历史鲜活起来的传统?

《司马迁来到B大历史系》新书首发座谈会现场,图为李开元教授发言
9月6日,《司马迁来到B大历史系》新书首发,一场题为“历史应当由谁来书写?”的座谈会在北京举行。该书作者日本就实大学教授、秦汉史专家李开元,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冬梅,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林鹄三位学者从历史叙事传统、学术体制反思、科学与艺术的平衡等角度,展开了深度而富有机锋的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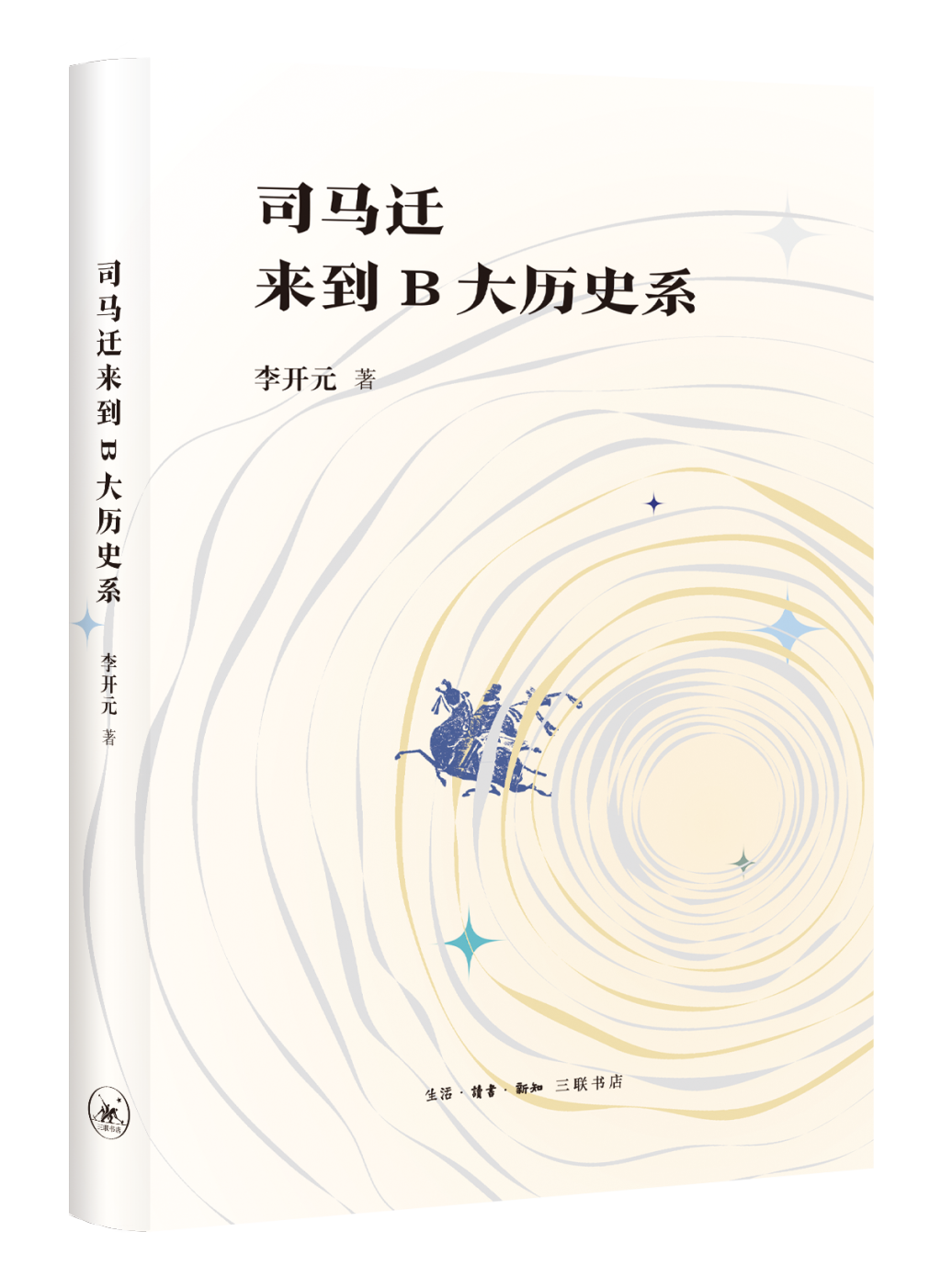
《司马迁来到B大历史系》书封
“研究和叙事是承载历史学的两个车轮,缺一不可”
在新书《司马迁来到B大历史系》中,李开元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和深刻的思考,讲述自己如何在四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完成了从历史研究到历史叙事的转向。这种他戏称之为“沦落”的变革,却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回归:打通文史哲,回到司马迁。

新书发布暨座谈会现场
李开元在发言时开宗明义,解释了这本随笔集的核心关怀与书名的由来。他坦言,“司马迁来到B大历史系”是一个文化寓言,旨在探讨一个尖锐的问题:若将《史记》置于当今偏重研究、强调科学范式的大学历史系评价体系中,其纯粹叙事性的伟大著作能否获得认可?“这种穿越式的设问,尤其能引发年轻一代对历史学本质的思考。”
李开元回顾了自身学术生涯的转变。他早期以《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等著作践行计量史学和科学主义研究,但逐渐感到此种方式虽提升了史学的科学性,却可能导致“心灵的枯竭”,使历史失去其鲜活的血肉与人文魅力。因此他毅然“变节”,从科学研究转向人文叙事,致力于创作《秦崩》《楚亡》《汉兴》等“复活型历史叙事”作品,“这不是对学术研究的否定,而是对太史公所开创的历史书写传统的接续,为历史学收复失地,恢复其源远流长的叙事传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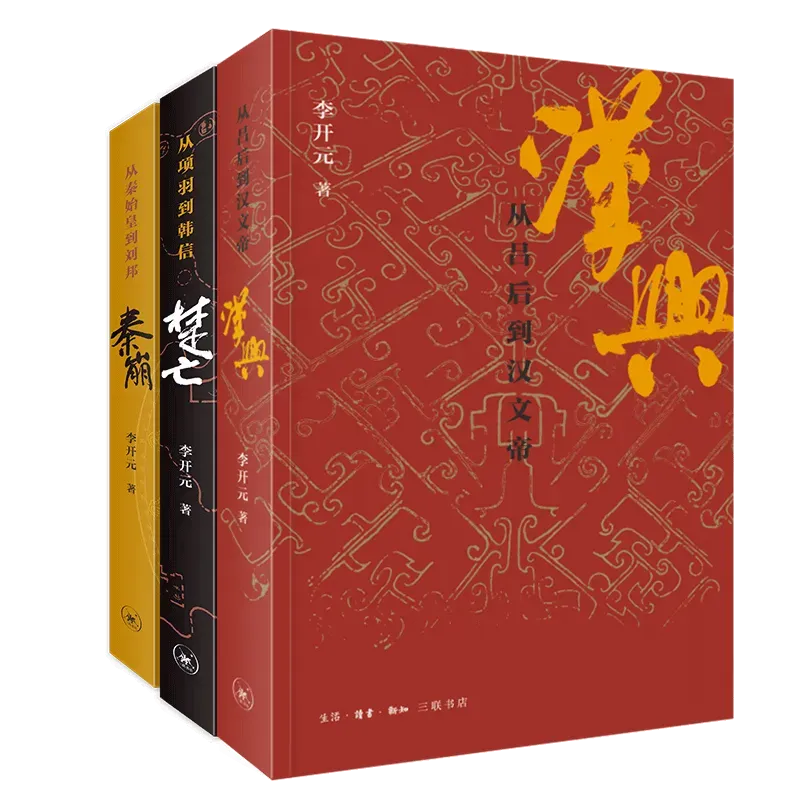
李开元所著历史叙事三部曲《秦崩》《楚亡》《汉兴》
对于当前历史学术体系将研究与叙事割裂、甚至扬研究而抑叙事的倾向,李开元先是表达了深深的忧思,“历史系不培养‘司马迁’,导致职业历史学家集体放弃了书写历史的公共责任,留下了巨大的空白,一度只能由媒体人或爱好者来填补。”
“但也应欣喜地看到,如今情况正在改变,越来越多的学院派学者如罗新、赵冬梅、王笛等投身历史叙事创作,已从‘涓涓细流’汇聚成‘滔滔洪流’。”李开元表示应该主张重新定义历史学,令其游走于科学与艺术之间,“研究和叙事是承载历史学的两个车轮,缺一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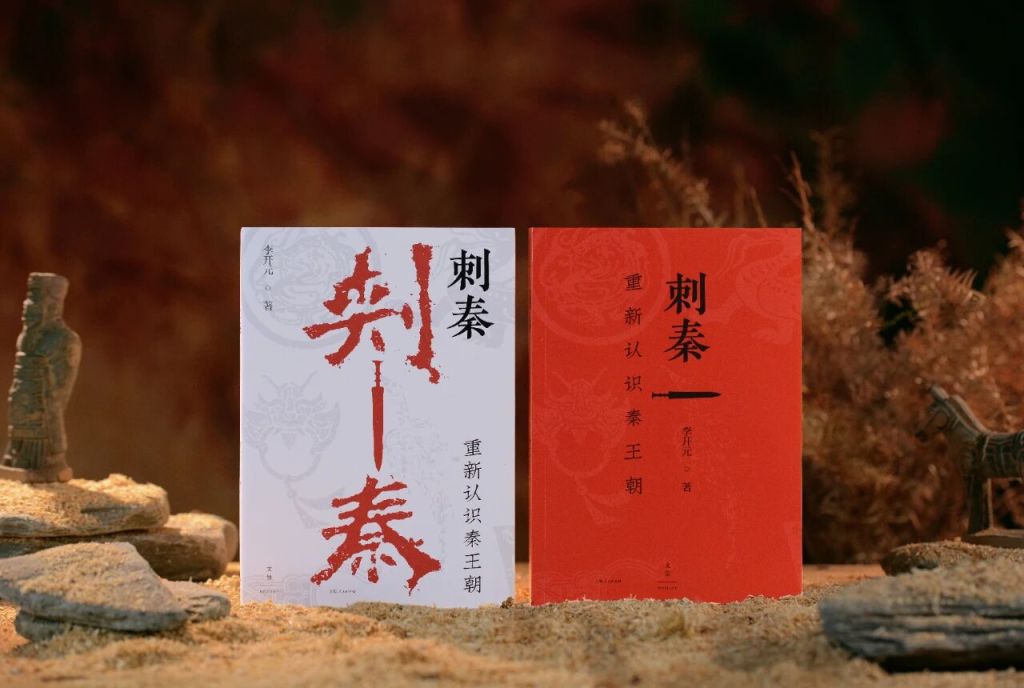
《刺秦:重新认识秦王朝》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5年8月
对于自身的历史叙事实践,李开元认为其《秦崩》《楚亡》《汉兴》“三部曲”是“可信可读的新形式史书”,并非通俗写作,而是站在学术研究最前沿的“历史再叙事”,其背后有详实的考据工作作为支撑。
而自己的另一本新书《刺秦:重新认识秦王朝》,他强调细节是历史真实性的重要载体,书中通过医学、兵器等细节考据还原出荆轲刺秦的场景,并认为口述史和现场考察,如与樊哙后人的交往,是司马迁获取生动细节的重要途径,而非纯文学虚构。
“历史叙事是在求真的基础上求美,完美地表现历史新知,传神地传达历史体验,这是一种至上的美的追求。”李开元说。
“伟大的文学作品有时比统计学著作更深刻、准确”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赵冬梅教授首先表达了对书名的“小小失落”——她最初期待这是一部司马迁穿越题材的长篇小说。但她随即肯定了该书的价值,认为其通过轻松易读的短文合集形式,如同与一位睿智的学者聊天,生动地揭示了传统历史叙事与现代学术研究之间的巨大落差。
赵冬梅结合自身实践,阐述了历史叙事的极高难度。她认为,历史叙事是一种“整合的历史,整体的历史”,要求写作者不仅对时代有深入研究,更能将各方研究融会贯通,并以深入浅出的文学化方式表达出来。“浅出的基础是深入”,这需要写作者兼具深厚的历史功底与文学修养,并且对现实社会有足够的感知和参与度。

《司马迁来到B大历史系》新书首发座谈会现场,图为赵冬梅教授发言
她特别强调了“细节”和“偶然性”在历史叙事中的核心地位。对细节的追问能推动研究走向深入,而历史进程往往是多种可能性碰撞下的唯一结果,其中充满了盲目的行动者基于有限信息做出的理性选择所交织出的偶然性。历史叙事者的责任,就在于呈现这个复杂的过程,而非简单地给出一个必然性的结论。
关于“历史由谁书写”的问题,以及如何评价公众历史传播,赵冬梅持开放态度。她认为,学院外的写作者同样值得鼓励,但前提是必须谦虚、认真地研读专业史学的研究成果,将其作为叙述的基础。同时,她也建议非学院派的创作者、自媒体作者,应该在作品中明确标注观点和史实来源的参考文献,为读者提供可追溯的线索,“这对创作者无损反而有帮助”。
作为李开元教授的“亲学生”,社科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林鹄在发言时认为,现代职业历史学模仿科学,追求客观精准,但其科学语言存在致命缺陷——无法表达某些至关重要的历史真实。
林鹄引用丰子恺游黄山鲫鱼背的感悟:照片无法表现高险的神韵,而绘画通过删繁就简、夸张改造,反而能“传神写照”。“同样,精确到厘米的数据,远不如‘万丈深渊’四个字更能传达人在险境的真实体验。这就像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小说家巴尔扎克的赞赏,伟大的文学作品有时比统计学著作更能深刻、准确地再现一个时代的社会面貌和精神。”
林鹄认为,李开元呼吁回归叙事、师法司马迁,其深刻意义在于促使学界反思模仿科学所带来的现代史学的利弊,而这必须深入到古今史学哲学基础的层面进行审视。
结合自身跨学科(计算机、人类学、历史学)的研究经历,林鹄也分享了关于“细节”的体会。他深感材料越丰富、细节越充分,对历史的理解就越可能突破既有成见,避免陷入空洞的“必然性”论断。“即便同时代熟人所写的传记,在细节上也可能极不靠谱,因此对细节的批判性考辨和深入把握,是获得关键性不同理解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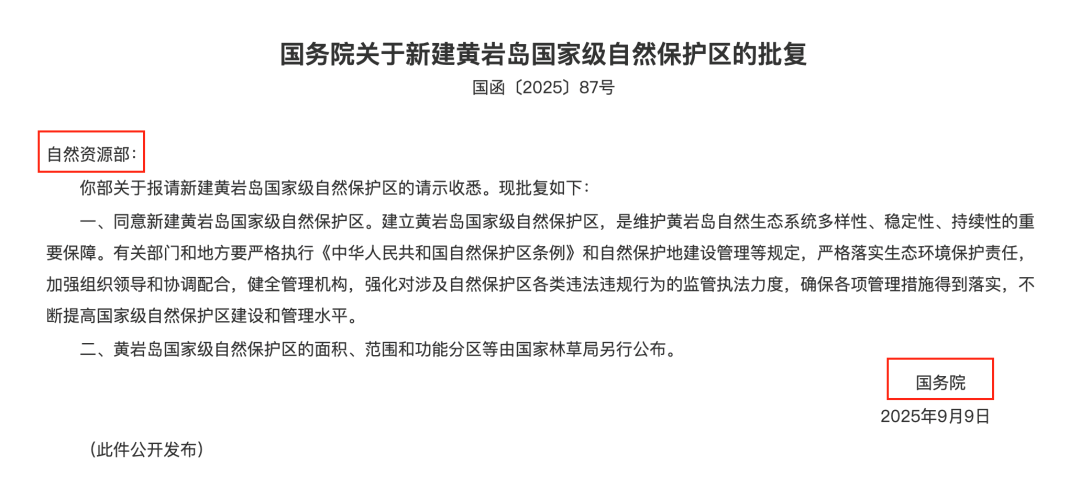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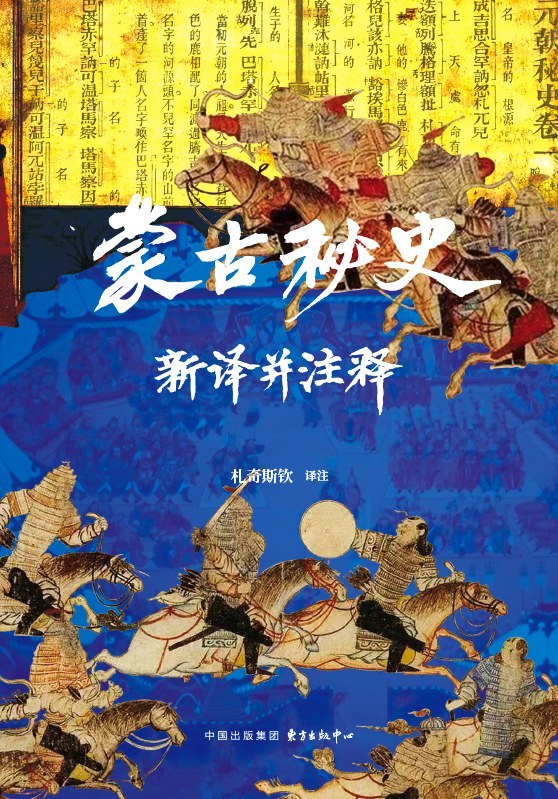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