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以为,古今中外所有作家中最令人着迷的一个群体,就是那些无法被归类的作家,英国作家埃利亚斯·卡内蒂正是这类作家的典型代表。卡内蒂的写作横跨了政治、哲学、文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个领域,他的小说《迷惘》(1935)和自传三部曲(1977-1985)是不朽的文学杰作,《群众与权力》(1960)早已被政治哲学界奉为经典,四部笔记《人的疆域》《钟表的秘密心脏》《苍蝇的痛苦》《汉普斯特德补遗》(1942-1985)则以格言式风格交织了文学评论、历史反思与个体观察,融汇成一个极深邃而庞杂的思想宝库。
同时,卡内蒂的个人身份也难以被归类,他1905年出生于奥匈帝国时期的保加利亚北部,却终生用德语写作,1938年加入英国籍,但归根到底是一位活在极权恐惧中的犹太人(祖先是居住在西班牙的犹太人)。这种犬牙交错的复杂身份造成了一个尴尬的结果:英国文学史少有对他的评价,而德国文学史也没有为他留下显赫的位置,甚至在卡内蒂获得1981年诺贝尔文学奖时,瑞典皇家文学院的授奖辞只能这样写:“卡内蒂,这位萍踪不定的世界作家有自己的故乡,那就是德语。”
纵观卡内蒂的一生,它几乎横跨了整个20世纪,其人生经历可谓极其复杂而丰富,而他也将所有的经历视为人生价值的源泉,正如他在自传三部曲的第一部《获救之舌》(1977)中的自白:“一个人的价值,蕴含在他自己已经经历和即将经历的一切之中。”而终其一生,卡内蒂始终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权力的本质。不同于诸多作家聚焦于极权体制的权力思考,卡内蒂则感到了另一股强大的力量——群众的威胁,而当时猖獗的德意法西斯,正是上述两方面的合流。就这样,卡内蒂在另一位来自东欧的犹太作家弗兰茨·卡夫卡身上找到了终身的思想和精神寄托。那些卡夫卡尚且感觉模糊的东西,对于卡内蒂来说已经变得非常明确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卡内蒂就是二十世纪的另一个卡夫卡。

卡内蒂
权力
欧洲人曾做过这样的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六十年来,地球上没有战争的日子只有26天。幸运的是,如今我们身处在一个和平的国度里,但放眼世界,国家地区间的战乱、族群内部的分裂、团体之间的争斗似乎从未停止。而所有这些战乱、分裂与争斗背后,始终回荡着一个关键词:权力。就在所有人都在思考极权体制中的权力问题时,似乎只有卡内蒂洞悉到了群众也可能成为一股可怕的力量,成为权力漩涡中的一股深不可测的暗流。“当我们在一个群众运动中丧失了自我独立性,我们就得到一种新自由——一种无愧无疚地去恨、去恫吓、去撒谎、去凌虐、去背叛的自由。”于是,当权力以不可控的方式运作,集体无意识取代个体思想,纷争与混乱便随之到来。
20世纪的人类历史充斥着集体迫害、群体狂热、世界大战等毁灭性灾难,凡此种种都不断推动卡内蒂开始思考群众与权力之间的关系,而这些思考的源头或许可以追溯到1922年的法兰克福。是年,工人领袖拉特瑙被右翼反犹分子暗杀,工人群众上街游行抗议。当时年仅17岁的卡内蒂竟身不由己地加入了人潮,这份亲身体验让他久久不能忘怀。他很纳闷,为什么一个有思想的旁观者,居然会无法抗拒这种“意识的彻底改变”,身不由己地受到人群强烈磁力般的吸引。这一思想好奇在他五年后亲历维也纳焚烧正义宫事件后变得更为强烈,以至于半个世纪后他在自传中回忆道:
那天的激情令我至今刻骨铭心。……我成为人群的一部分,我完全融入人群之中,对人群的所作所为完全没有丝毫抗拒。我真的很惊奇,即使在我当时心情激动的情况下,我还是能够清楚地把握我眼前的一幅幅情景。
这两个事件极大地影响了卡内蒂对群众与权力关系的思考,于是,他从1925年到1959年的34年间,断断续续地写下了影响深远的杰作《群众与权力》。与其说这是一部理论作品,不如说是一部夹叙夹议的长篇杂文,这在当时“科学性”风潮席卷群众心理学的背景下,显得是那么不合时宜。以至于他的好友布洛赫在1933年一度劝他放弃,“你花上一辈子的工夫,最后会完全没有结果。它每个地方都不牢靠。不要枉费时间了。你不如还是写戏剧的好。”但这本书就是他内心深处的某种情结,久久挥之不去,到54岁终于完成此书时,卡内蒂喃喃地写道,“这本书占据了我的全部成人生命,在我定居英国后的二十年,我断断续续地写这本书,几乎没有写别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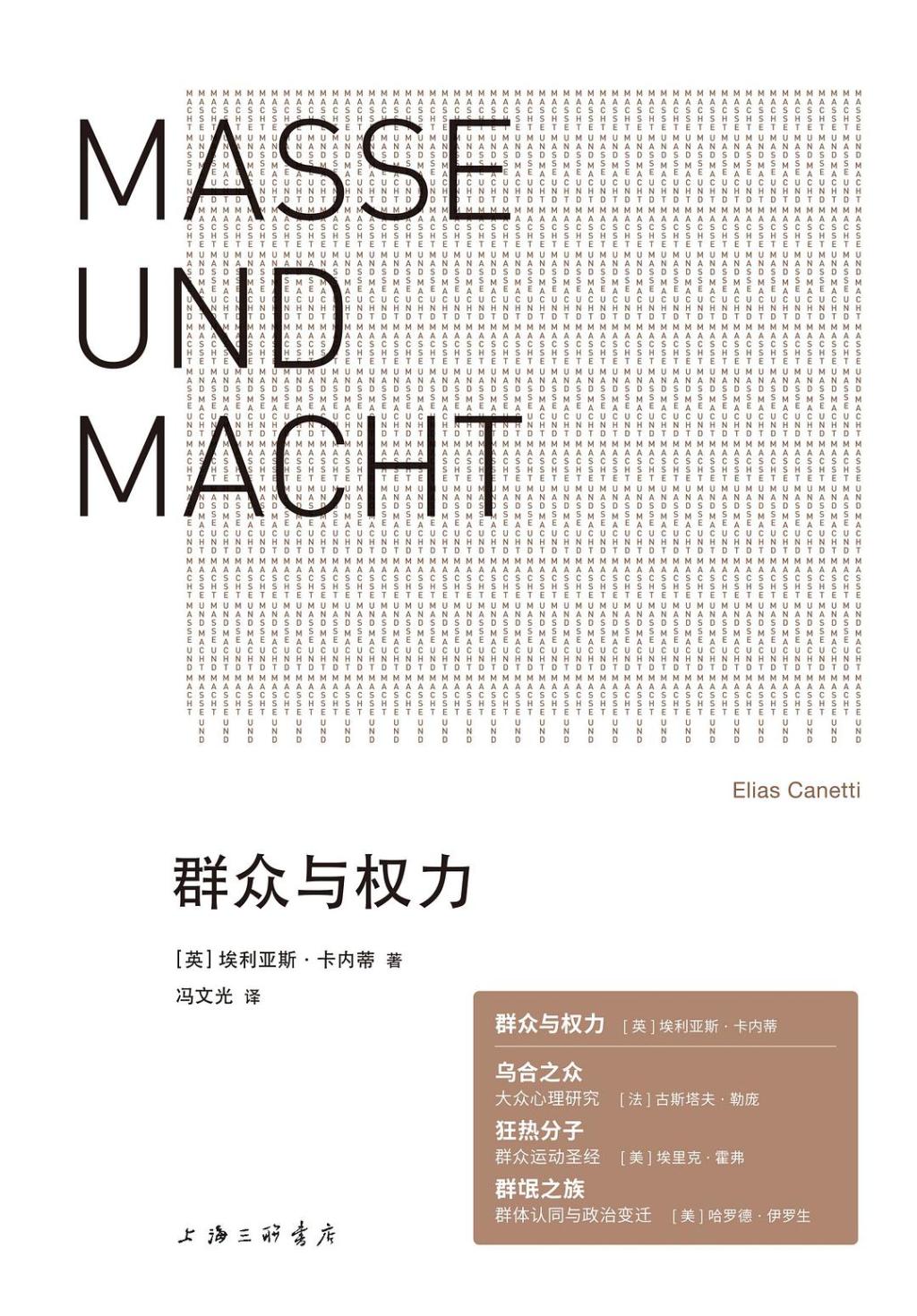
《群众与权力》
最终,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部与学院派风格极为不同的独特作品。卡内蒂采用了简洁且极富隐喻性的文学语言,内容广涉人类学、精神病学、生物学、社会学、哲学等诸多领域。其中,大部分是描述或叙述性的例子,来自全世界许多世纪的往事,经由他以完美的清晰和诗一般的优雅加以阐释。比如他写“权力的快感”,巧妙地用“牙齿”作表征。“权力首先必须能对别人的身体有伤害甚至消灭的威胁。权力就是把别人‘吃掉’,消化成对自己有用的营养,然后当粪便那样排除出去。文明遮掩了权力的粗鲁表象,但却在人的牙齿上留下了痕迹。人们进食使用的刀、叉都不过是牙齿的延伸。”每每读到这样的句子,仿佛是在读一位哲学家或诗人的某部作品。
整个20世纪,人们目睹了太多极具暴力性的群众行为。面对20世纪最让人困惑和痛苦的问题:平常的人怎么这么容易做出残忍的事情?卡内蒂极富创造性地用“指令”和“蜇刺”两个核心概念,来阐释现代群众以及群众与权力关系。在他看来,群众之所以会这些倾向,根本原因并不是群众本质恶劣,而在于权力对群众的伤害,对人性的侵蚀。权力向群众下达命令,群众往往因害怕而顺从。行为者每执行一道命令,都会在自己身上留下螫刺,但螫刺犹如下达的命令一样对他而言都是异物。无论螫刺附在人体内多久,它都不会同化,它仍旧是异己之物。而理想的群众、真实的群众恰恰时刻代表着与权力相反的存在状态。在真正的群众中,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没有人有权力命令别人。在此意义上,权力只是站在同志和敌人尸体堆上的胜利。
经历
1948年8月,卡内蒂在布莱恩斯顿暑期学校做了一场关于普鲁斯特、卡夫卡与乔伊斯的英语演讲。这次演讲可以被视为解读卡内蒂思考人类存在境况的一个关键文本。卡内蒂认为,那个时代的人类思想关注着三件事,一是我们的遗产,“去认识你的个人记忆所能带给你的一切吧,先把它填满,然后去探索它,消耗它,创造类似于你自己的记忆的科学,你将会成为过去的知识大师。”普鲁斯特对此做了最令人惊叹的探索;二是我们生活中的此时此刻,“乔伊斯开发了一种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他在预设的时间和地点的统一中,捕捉到了现在的流动:城市——都柏林;设定的时间——1904年6月16日。”三是即将发生的事,“对即将发生的事情,怀疑和忧虑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开的。恐惧是未来的预兆。在所有的现代作家中,卡夫卡是唯一在他颤抖的四肢里感觉到未来问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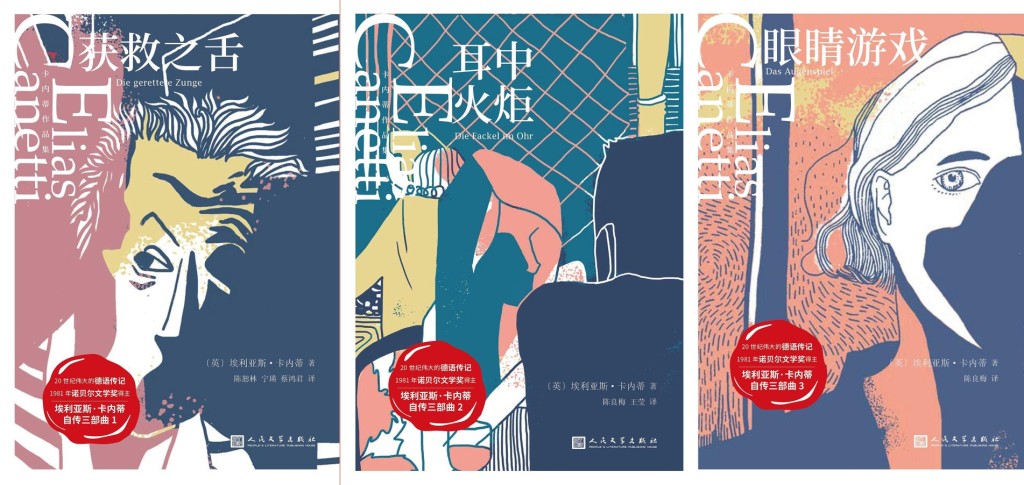
卡内蒂的自传三部曲:《获救之舌》《耳中火炬》和《眼睛游戏》
正是这种对已经经历、正在经历和即将经历的一切的重视,让卡内蒂试着将那些看似不相连的经历转化成琐碎的回忆,将深厚的情感与深邃的思想相互交织缠绕,这便有了被誉为“20世纪伟大见证”的自传三部曲:《获救之舌》《耳中火炬》和《眼睛游戏》。面对这个卷帙浩繁的系列自传,我们试图想象一个年逾古稀的白发老人,在面对生命的不断流逝与渐渐枯竭时,仍费尽心力地试图握住时间的轨迹。从幼年所住的鲁斯丘克开始回忆,战乱与家庭的变故,漂泊近乎流浪的生涯,一直写到生命中最重要的母亲逝世而停笔。最令人惊叹的是,人生际遇中那么多过客的名字与面庞,他都历历在目,亲切如昨。而他笔尖流淌出的每一段故事,更像是他对每一个人最细致的记录,还有这些人对他所产生的影响,或潜移默化,或根植于心。正如卡内蒂所言:
我尊重每个人的记忆。我想完整地、如其本来面目地保存它们,正像它属于每一个自由的人那样。
也许正是这份尊重与自由,塑造了其自传中丰富的思想性与艺术力量,并通过这些人所构成的人物群像中得到升华。就像以牙齿来隐喻权力,卡内蒂极为擅长以身体部位来隐喻某种存在的境况。在此,他以“舌”“耳”“眼”三种感觉器官串联起在不断的流亡、放逐和漂泊中度过的人生,它们共同见证了交织着苦难与辉煌的20世纪。卡内蒂六岁跟随父母前往英国定居,次年丧父,后来跟随母亲奔赴艺术与思想之都——维也纳,虽主修化学,却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从幼时留下的获救之“舌”到给予他深远影响的“火炬”杂志,再到隐于书报背后的那双洞察一切的“眼睛”,他品尝了时代的辛酸与苦涩,聆听了群众的呐喊和哀嚎,也见证了血与火的洗礼,生与死的轮回,最终在德语中找到了自己的皈依。
而所有这一切,都与一个人密不可分,那就是他的母亲。自传三部曲正是从他的母亲开始写起,并在母亲的葬礼处结束。《获救之舌》中的幼年卡内蒂对母亲有着无法抗拒的依赖与乖顺,虽然不曾达到普鲁斯特对于母亲那近乎变态的“掌控”,却也以一种“小兽”的警觉姿态,提防着每一位与母亲交往过密的陌生男性。而正是这种过分依赖的关系,让卡内蒂的教育受到母亲的巨大影响:母亲对于文学艺术的热爱就像一团火,也燃烧到了他的身上,他从文学作品中汲取营养,两人曾一度共同晚间读书,互相分享对莎士比亚等文学名著中的思考。也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母亲严苛地逼迫他快速学会德语,并使德语成为了他一生最重要的语言,甚至是他的精神故乡。
在《耳中火炬》里,卡内蒂渐渐学会思考,少年敏锐而叛逆的眼光终是将乖顺变成了分歧:他向往自由与平等,无论受到过怎样的教育,而母亲则注重自己的家族与出身;他走向了滚滚的人群之中,接受更多广博的知识与真理,而母亲却在慢慢衰老的过程中走向孤独的彼岸。于是,在最后的《眼睛游戏》中,卡内蒂迎来了妻子薇莎,却不得不目送母亲的慢慢逝去。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一个挽住他的手,一个却将其松开,卡内蒂试图“用声音换回她,而她也不能离开他”,婚礼进行曲与葬礼进行曲先后响起,预示着卡内蒂的人生迈入了新的阶段,也标志着这部“不同凡响的精神《奥德修斯》”的终结。
卡夫卡
如果说每个作家都有一位自己心心念念的偶像,会不自觉地去模仿、比较和对标,令他魂牵梦绕,念兹在兹。那么对于卡内蒂来说,这位教父般的人物就是弗兰茨·卡夫卡。1930年,25岁的卡内蒂初次读到卡夫卡的《变形记》和《饥饿艺术家》之时,其内心感受到的震撼,绝不亚于尼采初次读到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随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卡内蒂不断地赞美卡夫卡,一遍遍地读他的各种作品——小说、小故事、短章、日记、书信,甚至连别人对卡夫卡的回忆录都不放过。可以说,卡内蒂的全部文学活动,他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随时随地都受到卡夫卡的深刻影响,以至于他在1946年到1994年去世前的近半个世纪中,写下了大量关于卡夫卡其人其文的笔记、信件及文章,为世人呈现了两位德语作家跨越时空的思想联结。
卡夫卡一生中遇到的最大麻烦,或者说他感受到的最大困窘,乃是来自外部世界并转化成为其内在的精神心理现象的压力。进一步来说,卡夫卡所感受到的那种压力不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感受的局部的、琐细的压力,而是来自整个外部世界对个人存在的扭曲与变型。在他看来,一切的抗争都是徒劳,一切的行动注定失败。于是,我们在他的文集和书信中经常看到这样的句子:“一切障碍都能摧毁我。”“我最擅长的事,就是一蹶不振。”“我无法朝着未来前进,却能面对未来,裹足不前。”……因着这种彻骨的绝望,卡夫卡在遗嘱中嘱咐他唯一的朋友布罗德销毁他未出版的全部作品,已经出版的也不要再版——这意味着他打算亲手扯断他与眼前这个世界的唯一且极为脆弱的联系。在1964年12月的一则日记中,卡内蒂用一句话言简意赅地勾勒出对卡夫卡作品以至于他全部生活的印象:
要成为一个人,必须像卡夫卡那样变成一只虫,只能爬行,生活中一切都注定失败……他的境界是无能为力。
在此,卡内蒂将对卡夫卡构成压力的东西表述为广义上的“权力”,而后者正是卡内蒂用尽一生去思考的核心问题。对于卡夫卡来说,来自父权的压力构成了他一声中挥之不去的永恒阴影。“正是他父亲的权力散发出来的独特魅力,帮助他实现了这一目标,尽管这听上去如此残酷。他隔绝权力的方式十分特别,……他学会了让自己变小,小到最后消失;他的作品没有随他一起消失,这只是一个幸运的巧合。”于是,卡夫卡在面对这种几乎将他碾碎的压力时,选择了“无能为力”或“变成一只甲虫”来试图逃避,而当他退无可退之时,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那个被他称作“地洞”或“巢穴”的地方。
在所有关于卡夫卡的评论文字中,卡内蒂将他标志性的格言警句式的风格发挥到极致,其精彩纷呈的文字景观令人目不暇接。“《地洞》构成了卡夫卡所有元素的惊人统一。”“他由恐惧构成,他就是恐惧。”“‘直立的恐惧’——卡夫卡的这句话让我无法忘怀。”“通过明确而使事情变得不明确:卡夫卡的天分。”“无论他把脚踏在哪里,都会对那片地面有不确定感。”“他身上令人震惊、也让我不安的,是他稳定的成熟状态。”“他对于官僚权力的感觉,没有任何一个现代作家曾经以这种精确性和纯粹性表现过。”“成就卡夫卡的主要原因在于他没有意图,他成为作家不是出于生物性意志,而是出于假定的虚弱。”“他的残酷是一种非斗士的残酷,事先就感觉到伤口,一切都切入他的肉体,而敌人却毫发无损。”……
窃以为,上述的每一句评语都是打开卡夫卡心灵密室的一把钥匙。字里行间的指涉和意蕴,构成了卡内蒂关于卡夫卡和自己的另一种审判。这场旷日持久的“审判”显然是双向的,既是比较、审视,也是内省和独白,是卡内蒂与卡夫卡这位“残酷伙伴的对话”,是两颗近似的灵魂之间的低语,就像卡内蒂在1947年7月6日的日记中的自白:“‘在世’的作家里,卡夫卡是唯一与我贴近的,我对他像对一个老人一样欣赏。……当初幸好我既没读《审判》也没读《城堡》,不然我可能会陷入其中不能自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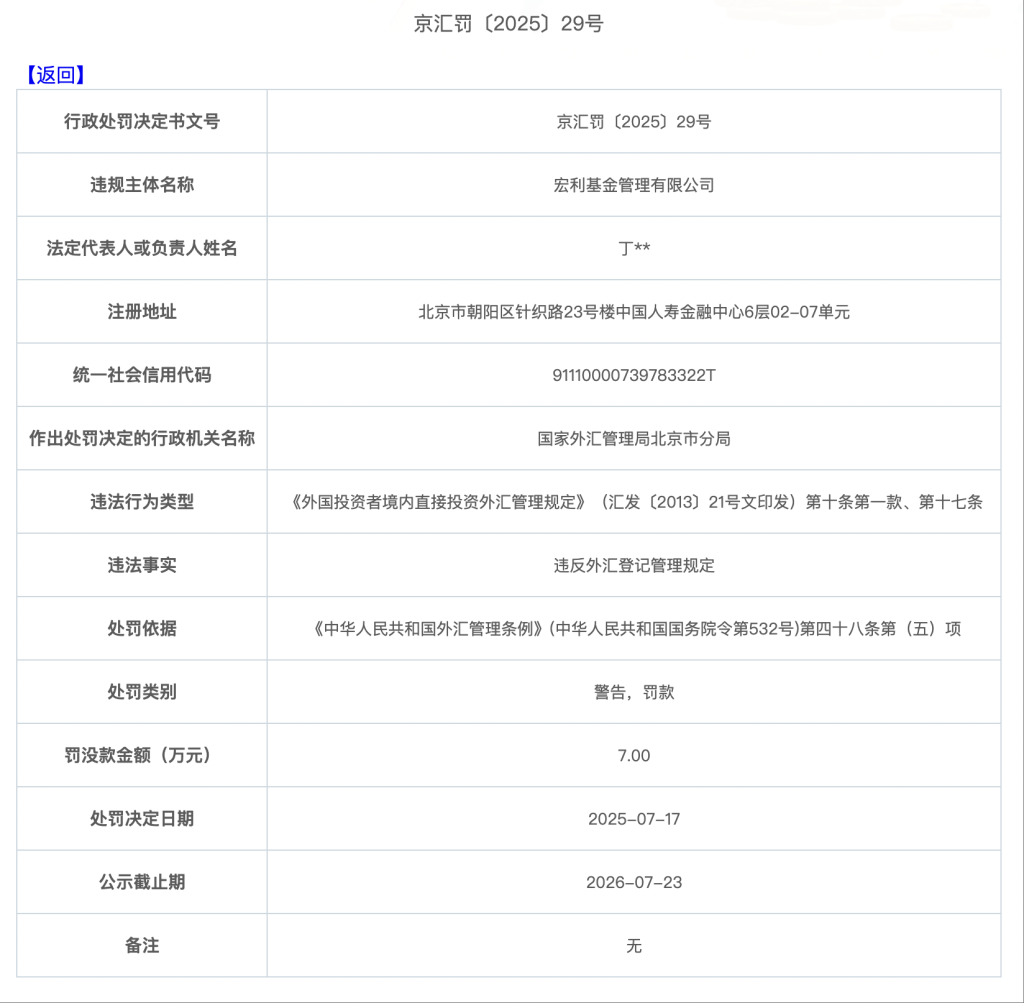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