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中期,我刚开始教书,记得语文课本里有一篇有关孔子的文章,提到由于汉武帝时的“罢黜百家”,才使孔子在历史上获得独尊的地位。这大概是民初新文化运动以后一般的看法。关于这一点,唐君毅先生与徐复观先生早已撰文批驳过。1975年,香港的报章、杂志曾争论孔子在历史文化中的原始地位的问题,这场争论,因是在中国内地“批林批孔”运动之后,所以徐复观先生在回应的文章中说“这是反映时代的争论”。“批林批孔”尽人皆知是政治斗争,但却引出一个有意义的问题,梁漱溟先生的《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的长文,就是在运动中(1974年)写成。二十年过去了,这个问题仍然值得思考,下文仅就汉以前孔子历史地位的形成,提出三点说明:

曲阜孔子博物馆门前的孔子塑像
(一)孔子个人的成就
要了解孔子历史地位的形成,这一点是最重要的,但首先必须排除一种观点。冯友兰先生于1930年代撰《原儒墨》一文,有谓“孔子虽自命不凡……而以继往开来、平治天下自命,但欲达其目的,仍必有人用之方可”。并引《礼记·檀弓篇》孔子将死时所说“明王不兴,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之言为证。根据《论语》,我们知道孔子的确热衷于仕途,总希望有人用他,以实现他德治与文治的理想,而这方面却是最失败的,依冯氏所说,孔子岂不是无成就可言,更不用说获得“天下宗予”的地位了。事实上恰恰相反,孔子是因坚持以道自任和“士志于道”的理想,才使他无法被时君所用,才使他四处碰壁,甚至有时候连生活都过得很凄惨,但他并未因此而丧失热情与自信。正因为他对自己理想的坚持,才为中国文化建立起一个用世不用世并不能决定人格价值及其历史地位的新标准,因而开启了一个人可以不用世,仍然可以有人生奋斗的目标,仍然可以有伟大的理想,仍然可以赋予人生以丰富的意义,仍然可以享有历史崇高地位的士人传统。
由“士志于道”的理想出发,孔子对政治上的用人主张尚贤。在这一要求下,“孔子打破了社会上政治上的阶级限制,把传统的阶级上的君子小人之分,转化为品德上的君子小人之分,因而使君子小人,可由每一个人自己的努力加以决定,使君子成为每一个努力向上者的标志,而不复是阶级上的压制者”。他不但主张尚贤,还培养了一批弟子,尽可能符合这个要求,这批弟子事实上也成为春秋各国尚贤政治下贤才之一重要来源。《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不侵》:“孔、墨,布衣之士也,万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与之争士。”此言虽嫌夸张,但孔子及其领导的士人集团,在春秋时代的尚贤政治中,确实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此外,孔子对中国文化最重要的贡献,是由于人格世界的开发,在诗、书、礼、乐的传承中,重建了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传统;由于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主体性的自觉,为社会秩序的重建提供了一套理论;由于首开民间讲学之风,为中国传统的教育精神、教育目标、教学方法奠定了不朽的基础。凡此种种,在以后相关的章节中,将有详细的讨论。
(二)弟子及继起者的尊崇
就《论语》看,孔子生前在时人心目中的形象,似乎很复杂,如仪封人以为“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好像是位神授超凡的人物。也有对他没有好感的,如微生亩当着他的面就说:“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佞人”是孔子最讨厌的;又如荷蓧丈人就把他看作“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之辈。当然,也有人把孔子当作圣人的,如“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不论时人如何看孔子,他的弟子对他是很尊崇的,子贡除了应和太宰语之外,有一次,他听到叔孙武叔毁谤仲尼,子贡的反应是:“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附带一句:孔子从未以圣自居,这正是他的伟大处,假如子贡这些话,当着老师的面去说,孔子必定不会同意的。
孔子身后,门弟子的情况,据《史记·儒林列传》的记载:“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所谓“子路居卫”,是明显的错误,因子路比孔子早一年已去世。至于孔门弟子人数,《史记》所载并不一致,《孔子世家》:“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仲尼弟子列传》:“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而据《论语》,比较能确定为孔门弟子者,有二十二三人。《史记》的记载虽未必都可靠,但说弟子们“散游诸侯”,这本来就是孔门宗风,当然可信。因弟子们散在四方,因而扩大了孔子的影响力,也是可以想见的。不过,在孔学的继起者之中,有两位大思想家——孟子与荀子,由于他们在战国时代特出的地位和思想上的杰出成就,对孔子历史地位的形成,其功比孔门众弟子,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
孟子是一位充实而有光辉的人物,我们在两千多年后读《孟子》,仍然能感受到一股逼人的光焰。孔子欣赏木讷,讨厌佞人,孟子却滔滔雄辩,“恶声至,必反之”。他与孔子一样,都有永不衰竭的救世热情,但比孔子更加自命不凡,觉得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孔子开启了“士志于道”的理想主义的传统,孟子所塑造的人格典范,则为这个传统注入强大的动力。这样一位不可一世的人物,对孔子却完全心悦而诚服,所谓“乃所愿,则学孔子也”。也赞同孔门弟子宰我、子贡、有若“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的颂扬,他对孔子的总评断是“圣之时”与“集大成”,从此成为历史定论。
荀子与孟子虽皆传孔子之道,但人格类型与学问性格大不相同。在人格上,孟子凸显的是道德的光辉,荀子凸显的是理智的光辉。孟子所传之道,须向身心上内求,因而奠定了内圣之学的基础;荀子所传之道是由“礼义之统”来彰显,是一种制度性的客观标准,也是认知的对象。因由心性出发,故孟子倡性善之说;荀子为发挥礼义的功效,故主张性恶。孟、荀虽仍未能实现理想,在现实上其地位的崇隆,已非孔子当年可比,孟子周游列国、游说干君之日,往往“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齐宣王时出仕为卿,享万钟之禄。荀子在赵国贵为上卿,当齐稷下盛时,曾三次被推为祭酒,领袖群伦。孟、荀在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不但树立起儒家巨擘的地位,也确实能发扬孔子的精神与孔子的学说,使其光耀后世。
孟子宣扬孔子的伟大,使用类似宗教的语言,荀子尊崇孔子,使用的是历史的语言。在《荀子·儒效篇》中,他把儒分为俗儒、小儒、雅儒、大儒,称得上大儒的,只有周公、孔子。他认为孔子之所以能“名垂乎后世”,是因他“诚义乎志意,加义乎身行,箸(著)之言语”,也就是说,他的言行志意都符合礼义。荀子对孔子最大的尊崇,是说他“德与周公齐”,所以然者,是因“孔子仁知且不蔽”。周、孔并称,与后世的孔、孟并称,其精神、其内涵是大不相同的,就孔子的终极理想而言,周、孔应优位于孔、孟。

孔子“圣迹图”
(三)墨、老、庄、韩的褒贬
战国时代,孟、荀之外,各家对孔子皆贬多于褒,此或如苏轼所说,乃“阳挤而阴助之”。盖言不论是褒是贬,已使孔子成为箭垛式的人物,俨然居于历史的中心位置。
先说墨子。《淮南子·主术训》:“孔丘、墨翟修先圣之术,通六艺之论。”他成长的大环境,也与孔子相似,但思想取向与人格特质,二人大不相同,这与墨子出身于下层社会有很大关系。战国初年,对士人阶层提供了自由发展的环境,下层社会的百姓的生活却更加困苦,墨子就从一般百姓的感受出发,主张节用、节葬,又非礼、非乐、非儒,孔子心目中辉煌的周文传统几乎成为反面教材。孔、墨之间最尖锐对立的是伦理观,孔子的伦理观发之于宗法传统、家族组织,讲求亲疏、差等;墨子的伦理观建基于墨者团体,他反宗法、反封建,以兼爱代替差等之爱,最重要的价值观念,不是孝、弟、忠、信,而是正义、公道、平等。如果说孔子是一位伟大的道德与人文的教师,墨子扮演的则是一位苦行卓越的社会改革家的角色。必须指出,墨子虽因不利于国家百姓之利而非议礼乐,但对相传“制礼作乐”的周公,仍称其“为天下之圣人”;有一位叫程子的人曾问墨子,你既然非儒,为何又称道孔子?墨子回答:“是亦当而不可易者也。”可见他承认孔子确有其“不可易”的价值在。
次说老、庄。读了《论语》《墨子》,再读《道德经》,其文字风格及其揭示的意义世界,与孔、墨大异其趣,直觉的印象是,老子的思想与殷、周的文化传统,在历史的纵贯上,几乎没有什么关联。他不托古,也不提以往历史上的人物,他超越了传统,也不存心与其他学派为敌,有些地方好像是针对儒家而发,其实他只是利用现成的素材、已流行的观念,表达他自己的思想。他没有孔、墨那样的救世热情和使命感,他冷眼看乾坤,洞悉现实政治、社会、人生的奥秘,即使以现代的标准去看,他依旧是一位具高度智慧的哲学家型的人物。
从《庄子》书中所了解的庄子,是中国思想史与文学史上不世出的天才,他那丰富新颖的概念,纵横奔放的想象力,奇诡独特的文体,在在都表现出他的独创力。他追求生命的本真,向往超越、自由的心灵世界,为中国文化注入一股异于儒家的活力和精神。《庄子》书中所反映的孔子,正如庄万寿先生所说,“充满道家的主观偏见”,“充满揶揄、攻击孔儒的文字”,特别是《渔父》《盗跖》《胠箧》三篇。孔子重视仁义,庄书“直视仁义是心乱的根源”;孔子推崇三代礼义法度,庄书视之“如取先王已陈的刍狗”;孔子不耻下问,学无常师,“在庄子书中被写成为没有自我,唯人是师的庸才”。此外,孔子学于老聃之事,于《德充符》《天地》《天运》《天道》《田子方》等篇中出现多次,其中牛头不对马嘴的对话,可以当幽默、滑稽的文章欣赏,没有人会当真的。倒是有一点值得提出来,即孔子为何在《庄子》书中“被塑造为宣扬道家思想的主角”?我们对古人的动机、心理,无意妄加揣测,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假如孔子在当时没有显赫的声名,假如孔子在他们的心目中不占有一定的分量,是绝不会这样去做的。
再说韩非。萧公权先生早已指出,“韩非术治为吾国古代最完备之专制理论”,“就先秦历史背景言,则为法家思想之最高发展”,“就近代法治思想言,不免为‘祖型再现’之退化”。从近代民主法治的观点看韩非,他当然代表一种负面的思想系统,在历史层次上,韩非政治哲学的价值不能抹煞。因是专制理论,遂处处与儒家对立,儒家主性善,韩非主性恶(主性本恶,与荀子性恶义不同);儒家尚贤,韩非坚决反对;儒家重德,韩非重力;儒家主张德治,韩非主张法治(法乃帝王统治人民的工具);儒家尊古,韩非薄古;儒家重理想,韩非重功利。
根据徐复观先生《韩非心目中的孔子》一文,《韩非子》直接提到孔子的约二十九次,提到孔子而正面加以批评的有两次:(1)《八说篇》:“博习辩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则国何得焉?”(2)《忠孝篇》:“臣曰:孔子本未知孝悌忠顺之道也。”《显学篇》在反对的同时又说“孝戾侈俭,俱在儒、墨,而上(人君)兼礼之”,反映韩非也承认孔子在战国时代,被人君所尊崇的地位。《内储说下》引了孔子治鲁、齐人献女乐的故事,而承认“仲尼为政于鲁,道不拾遗”。《五蠹篇》在推崇“仲尼,天下圣人也”之后,又说孔子的仁义,不如鲁哀公之“势”所生效力之大,所以政治应重“势”不重仁义。韩非虽不像道家之徒借孔子来宣扬自己的思想,孔子在他心目中有一定的分量,是不成问题的。
孔子在秦、汉之际的地位,在此也不妨一提。号称“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的《吕氏春秋》,杂采战国时期众家之说,但称引次数最多的人乃是孔子(引述孔子五十多次、管仲三十次、墨子二十次、老子五次、惠施十五次)。秦始皇焚书坑儒,这事件本身就说明儒者们在秦廷有一股庞大的力量。儒者虽死,儒教却影响了秦帝国的社教政策。秦始皇一统天下后,游幸所至,皆刻下碑文,宣扬国威,同时也重视社会风教,如泰山刻石、会稽刻石、峄山刻石,无一不是儒家“明教化、正风俗”之礼教的实现,所以顾亭林说,“而其(指秦始皇)坊民正俗之意,固未始异于三王也”。刘邦打天下时,极端轻视儒生,但高帝十二年,“过鲁,以太牢祠孔子”。由此可见,汉武帝时的尊儒运动,不过是顺应数百年来历史之势,使尊孔纳入国家体制而已。
本文摘自著名哲学家韦政通所著《孔子传:华夏的崩坏与新生》,为该书“绪论”的部分内容,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刊载,注释从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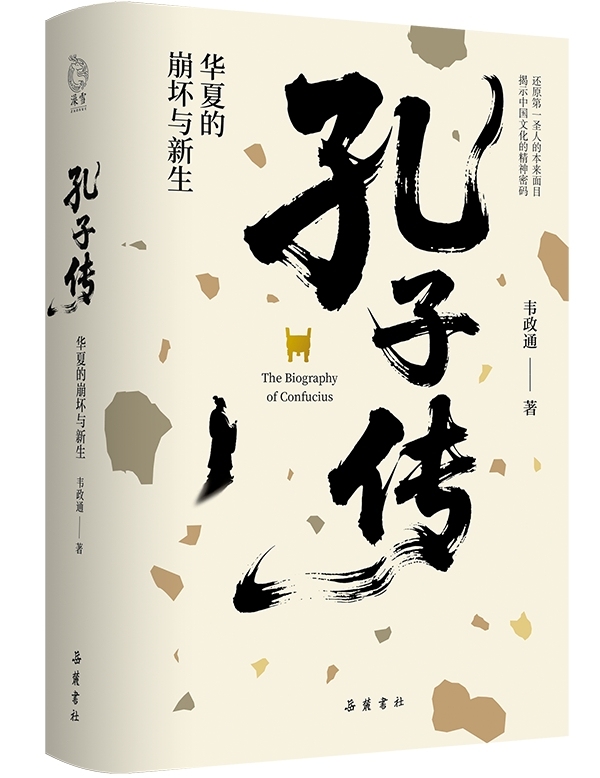
《孔子传:华夏的崩坏与新生》,韦政通/著,岳麓书社,2025年8月版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